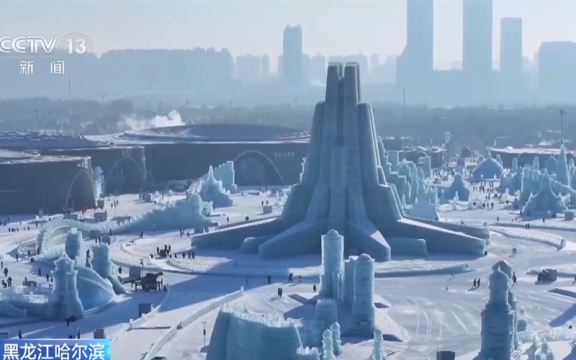建党之前:陈独秀在上海(4)
陈独秀认为,救中国、建共和,首先得进行思想革命,而要改变思想,须办杂志。他放弃安徽舒适的生活,再次选择在上海“蜗居”,心里是有着创办一个大型出版公司兼营杂志的一揽子规划的。这个事业似乎只有在上海才能完成。此时的上海已是中国出版中心,全国出版业的80%以上集中在这里,形成了比较完善的出版市场,从著书、编书到印刷、发行,都相当齐备,具有其他城市无法匹敌的优势。抵达上海的第二天,陈独秀就投身于这项工作,陆续与一些同乡、好友进行商量。经过一段时间的奔走,这一宏大计划虽然没有完全实现,但出版一本杂志作为计划一部分得以先行。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个一揽子远期目标,1915年,群益书社才会在并无赚钱胜算的情况下,慨然投入每月编辑费和稿费200元来出版《青年杂志》,第二卷起改名为《新青年》。
当时上海市面上能看到期刊、报纸数不胜数,从中脱颖而出,决非一件简单的事。至于《青年杂志》为何不合常理,很快更名,据云是因为当时上海的基督教青年会看到《青年杂志》出版,来信投诉,认为“群益(书社)的《青年杂志》和他们的《上海青年》(周报)名字雷同,应该及早更名,省得犯冒名的错误。想不到‘因祸得福’,《新青年》杂志和他们的宗教十分浓厚的周报更一日日的背道而驰了”(汪原放:《回忆亚东图书馆》)。
上海的法租界虽然秉承“出版自由”的价值,但也并非绝对安全的飞地。1914年12月袁世凯政府颁布的《新闻法》明文规定:任何新闻工作者触犯了“国家安全”“社会道德”和“社会福利”都将被视为罪犯。杂志初创的第一年里,陈独秀非常小心地不直接涉及政治运动,甚至连反儒家思想运动也暂不开始,而是集中精力召唤中国青年来注意西方进步的新思想。这本启蒙杂志不再有教无类,目标读者群体是非常明确的。在首期《敬告青年》一文中,陈独秀解释了“新青年”对一个国家的重要性。青年是社会里最富生命力的成员,因而在社会现象中是有着决定性作用的。他希望看到的中国青年是“自主而非奴隶的、进步而非保守的、进取而非退隐的、世界而非锁国的、实利而非虚文的、科学而非想象的”(《敬告青年》,《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以后数年中,陈独秀一人于上海所办的《新青年》,号召“民主”“科学”“反孔”和“文学革命”,以欧美国家——尤其是法国——为模范,以期使得沉落的中国能够民族复兴,快步迈向一个现代化的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