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魏晋到晚明:寻找被压抑的抒情之声丨专访孙康宜(3)
新京报:所以我们是不是可以把晚明的这种个性解放与女性诗人的自我表达,视作中国文学现代性的一种先声?
孙康宜:我认为可以这么说。虽然在美国的文学系看来,把明清文学算作古典文学还是近代文学是一个值得商榷的问题。所以我们发明了一个名词叫做早期现代(early modern),但是我很同意王德威教授的说法,研究现代文学要从明清开始。正所谓“没有晚明,何来晚清”。而这种现代性我觉得与王阳明的心学有莫大的关系,因为王阳明的“发明本心”其实有着发现人的主体性与自我意识的用意。而晚明知识分子的结社其实与现代社会的观念有很多类似的地方。
其实中国文学中所谓寓言的传统源远流长。比如曹植的《洛神赋》在我看来,一定是爱情诗。曹植把爱人比作美丽的水鸟,哀悼她的伤逝。可是在中国的阐释学传统中,却偏偏认为这首诗是曹植写给曹丕的,表达自己怀才不遇。中国的阐释学传统开启于《毛诗》,汉代儒学家注疏《诗经》的时候贯彻了孔子的“思无邪”和“兴观群怨”的教化思想。所以很大程度上《诗经》尤其是《国风》中的浪漫色彩是被削弱的。所以英国的翻译家亚瑟·威利在翻译《诗经》时就一直强调,我们不应该把《诗经》当做寓言,而应当直接当做抒情作品。而到了明清时代,这种阐释学的传统逐渐受到挑战,我们从陈子龙等人的诗歌中可以找到更真挚的表达,感到一种与现代人表达情感类似的方式。
新京报:无论是陶渊明、谢灵运还是庾信,在后世都成了诗人模仿与赞誉的对象。比如苏轼对陶渊明的喜爱,王维、孟浩然的山水诗也继承了谢灵运对“风骨”的追求。而杜甫在晚年对庾信有着感同身受的体会。陶渊明所代表的田园诗,谢灵运所代表的山水诗,以及庾信的家国情怀其实是中国文学的重要母题。我们是否可以得出结论,中国文学重要的传统与母题,其实早在魏晋时代就已经奠定了雏形?
孙康宜:我觉得可以这么界定魏晋文学的地位。按照奥尔巴赫的说法,西方文学也是分为两种模型(model),一种是希腊罗马型的,一种是《圣经》型的。在中国的文学传统中其实也存在这种模型。比如田园诗,就受了道家思想的影响,谢灵运的山水诗是汉赋型的。
如果我们把诗歌比作一个圆圈,那么陶渊明是努力探索圈内的部分。他试图找到心灵的平静与秩序,而谢灵运是努力把圆圈的范围扩大,在外部世界找到心灵的自由。你看谢灵运的《山居赋》,里面全然是他为自己构筑的一个精神世界,其中有山有水有动物。他希望借此塑造一个世界,这就是受到了汉赋的影响。陶渊明的诗非常短小精悍,但是足够表达他的精髓。所谓“欲辨已忘言”,其实是说他回归到了田园,真正地摆脱了外部世界,成为一个隐士。到宋代时,随着理学与士大夫品位的兴起,陶渊明才变得重要。苏轼把陶渊明视作偶像。但在唐代,陶渊明是很边缘的。杜甫就曾经批评陶渊明:“陶潜避俗翁,未必能达道。观其著诗集,颇亦恨枯槁。”他认为陶渊明放弃了出仕的理想与追求,未必真的成就了“道”,所以“未必达道”。然而到了宋代,苏轼等人提高了陶渊明的地位。但我个人的认为(也是高友工先生的想法)是:杜甫的人生观与陶渊明很不相同,他一直忠君爱国,以出仕作为他的最高理想。我以为杜甫误解了陶渊明,而苏轼才是真正了解陶渊明的人。
然而到了明清时代,庾信的地位被重新发现与肯定。尤其是晚明与魏晋在时代背景的相似,比如少年诗人夏完淳就写过“苏属国(苏武)之旄节终留,庾开府之江关永弃。”以此表达自己抗清的立场,而他的《大哀赋》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哀江南赋》的模仿与致敬。陈寅恪先生认为《哀江南赋》是中国文学最重要的作品之一。
新京报:其实唐代文学也在某种程度受到魏晋文学的影响,比如初唐文学盛行“江左余风”,诗就受所谓庾、徐流派的影响很深。包括古文运动,也是要打破六朝文学旖旎绮丽的风格,回归质朴和简白。无论是继承还是超越,我们可以看到,南朝宫体诗的影响对唐代文学的风格影响甚深。作为中国诗歌的高峰,唐代文学与魏晋文学又是一种怎样的关系?
孙康宜:唐初的诗人也许在有意识地模仿宫体诗。但当时的批评家认为这些都是靡靡之音,而唐初的诗歌只是一味地模仿。杜甫偏爱庾信,所以某种程度上杜甫通过对庾信的评价,提高了宫体诗的地位。但是庾信晚年的诗歌与早期不同,尤其是他被掳去北周之后,问题完全变了。庾信早年在萧纲的影响下,写的是宫体诗。但是他晚年的风格则是清新质朴的风格,尤其是很多诗歌以陶渊明作为榜样。
也许很多人会认为,宫体诗是作为宫廷礼仪的一部分,并且有着严格的格律,很难有个人抒情的空间。但我认为,只要是诗歌就一定会有抒情的部分。因为诗歌的目的一定是“诗言志”。比如庾信的《咏美人看画》中的“欲知画能巧,唤取真来映。并出似分身,相看如照镜。安钗等疏密,着领俱周正。不解平城围,谁与丹青竞。”其实就表现了对自己的身世和命运的感慨。如果我们看萧纲为《玉台新咏》做的序(“既而椒宫苑转,柘馆阴岑,绛鹤晨严,铜蠡昼静。三星未夕,不事怀衾;五日犹赊,谁能理曲。优游少讬,寂寞多闲。厌长乐之疏钟,劳中宫之缓箭。轻身无力,怯南阳之捣衣;生长深宫,笑扶风之织锦。”)我们就会发现宫体诗预设的读者其实是宫廷中的女性,所以在宫体诗里发现大量对女性容貌的描写,但宫体诗不见得所有的部分都是描写,一定会有属于个人抒情与思考的空间。
新京报:诗史是中国文学的重要传统。优秀的文学作品一定会成为史学家的史料与研究对象。比如陈寅恪先生就借用明清士大夫的诗文写就了不朽名作《柳如是别传》。你曾把陈子龙的诗歌称为具有悲剧感的历史观念。我们应该如何在文学作品中感受并理解历史的存在?
孙康宜:我之前在普林斯顿读书的时候,我的老师高友工和牟复礼一直强调,研究文学的人一定要随时想到历史,研究历史的人绝对不能离开文学。这二位先生对我影响太深了,我一直认为文史不分。

电影《柳如是》(2012)剧照。
我在写陈子龙和庾信的时候,一直注重描绘他们的历史背景。我感兴趣的是,什么样的时代与环境,会激发出庾信和陈子龙这种天才的想象力与创造力?我训练学生的时候一直对他们强调,不仅要看到文学本身,还要看到历史。我一边让他们注重文本细读(close reading),一边希望他们注意文本生成的时代。只有南朝与北朝对立的时代,才会让庾信写下那么伟大的作品,而造就庾信的,还有他独特的经历,如果不是侯景之乱,庾信无法回到故乡,他也无法写出《哀江南赋》中那么独特委婉的感情。正如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所说“此人皆意有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司马迁、庾信、杜甫、陈子龙,都是经历了苦难之后,才创作出他们最伟大的作品。这些作品都是饱含着他们在一个大时代中流离、挣扎的痕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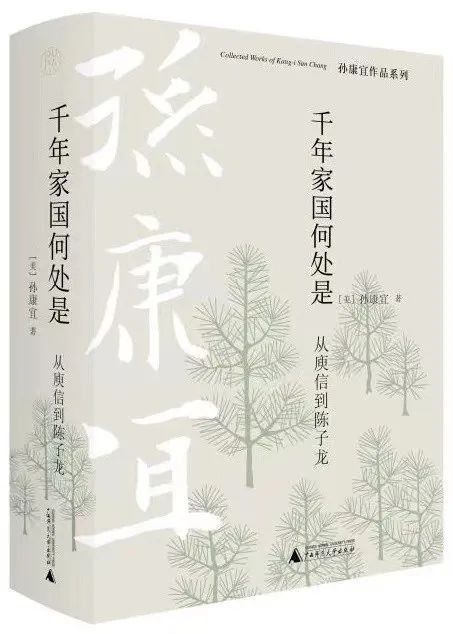
《千年家国何处是:从庾信到陈子龙》,[美]孙康宜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7月版。
所以中国古代的注疏者,常常把这些充满个人生命经验与个人色彩的文章解释为爱国诗,或者引申为一种政治抱负。我不认同这种说法,我更希望我的读者能把文学与历史放在一起,去感受读解这些诗人在山河鼎革之际的个人体验。
新京报:阅读晚明时代女性诗人的作品有一个发现,就是她们往往会把自己当做一个男子去看待。而看士大夫的诗文,他们却经常借用女性的意象和典故来抒怀自己的命运和对于时局的忧虑。通过这种现象,我们会不会觉得所谓女性诗人的出现其实改变了中国文学的抒情传统,是一种更直接的传统?
孙康宜:我认为明清文学中的性别观念是中国文学中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如果说我在美国的研究有什么贡献的话,我认为是这一点。因为转变的不只是性别观念,还包括我们刚才聊到的“情”的观念,以及“清”的观念。“清”就是清洁、高远,萧条方外、不与俗世萦怀的意思。在魏晋时代,“清”是只属于男子的评价,比如阮籍、陶渊明。但是到了明代,这个观念就不再仅属于男性了。相反很多男性因为政治的腐败选择不参加科举考试,反而赞助自己的妻子的文学事业。比如陆卿子和王端淑的丈夫赵宦光与丁圣肇,他们都过着隐士一般的生活。
1993年夏天,我与魏爱莲教授合办了耶鲁明清女性文学国际研讨会,网罗了海内外优秀的明清文学研究者。而为了更好地研究中国文学中的女性诗人,我与我的学生苏源熙编纂了《传统中国女性作家:诗歌批评选集》(Women Writers of Traditional China: An Anthology of Poetry and Criticism)一书。所以明清文学在我的研究中一直是最重要的,而且我关注的不仅是女性意识,而是为什么这样的时代,会使得女性有自我意识解放与觉醒的机会去写作。藏书家胡文楷收集到16—19世纪的女性诗人作品一共有3000种之多,我后来跑遍了美国国会图书馆、耶鲁图书馆、哈佛图书馆,甚至请人专程去日本找王端淑的《吟红集》,收集到的也只有胡文楷先生的5%那么多。
新京报:正如你刚才所言,中西文学有着不同的思维模式。你在向西方的学生讲授中国古典文学的时候,会不会感到一种语境和文化上的隔阂。或者说,你在与西方学者和学生交流的时候,如何向他们解释中国文学普遍性的价值?
孙康宜:我总希望把中西文学放进一个比较的视野和框架里看,我面对的学生大多是本科生,他们也不懂中文,但是他们上了两周课之后自然就会发现《诗经》《楚辞》都懂了,因为文学有一些跨域语言和国界的共通性。我在讲课的时候会让他们比较同时期的西方文学发生了什么,我在讲杜甫、苏轼的时代,英国文学才刚刚开始。自然而然他们就会通过比较了解到中国文学的魅力在哪里。很多学生通过我的《人与自然》这门课对中国文学有了新的认识。比如我许多的学生,他们现在都是汉学界鼎鼎有名的人物,但是他们最早对中国文化的兴趣都是由此开始的。
采写袁春希
校对薛京宁付春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