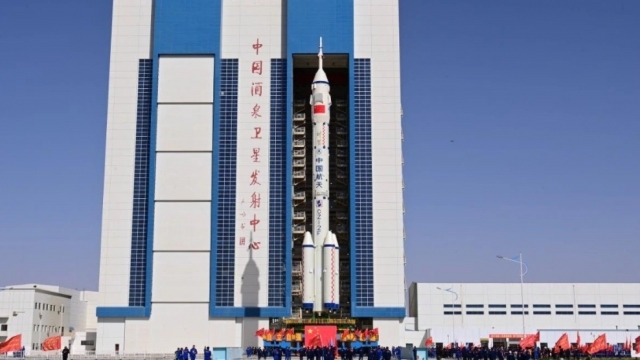从魏晋到晚明:寻找被压抑的抒情之声丨专访孙康宜
伟大的文学作品往往诞生于危机与转折的时代,在时代的动荡与波折中经历了生命的脆弱与价值的荒谬,经常是诗人意识的觉醒。在这种环境下认识的环境与人生,不再执意于现世与道德、历史的视域,而具有一种终极性的追问,走向个体人格的最终归宿。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断裂与开创,叛逆与超越并存的时代。也正是在这样山河易色的背景下,知识阶层逐渐由追求标准的人格理想,转而寻求个人精神的独立与自由。如果在“政统”与“道统”中无法找到安放个人理想的空间,何不在审美与自然的世界中恬然鼓腹,从欲而欢?如果仁义礼教中,找不到宇宙与形而上的终极关怀,也无法回应现实中的眼泪与伤逝,在失意与适意中浅吟低唱的诗人们,也许会欣然发现自己的生命感觉寄存于山水和情爱之中。
魏晋南北朝的文学与精神气质,是中国思想史与文学史中的异类。在时代的剧变与知识阶层的苦闷中,中国文学第一次找到了自己心灵的声音,士大夫的个体意识从群体自觉中解放出来,渴望在内心的幽微之处找到任情与适性的自由。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下,中国文学开创了属于自己的抒情传统。这个边缘与叛逆的时代所孕育的边缘的诗人们——陶渊明开创的田园诗、谢灵运开创的山水诗、庾信诗赋中悠长延绵的家国意识与易代之悲——成为了后世的诗人们缅怀与回望的传统。

本文出自《新京报·书评周刊》9月16日专题《风景不殊——魏晋时代的文学与抒情》的B02-B03版。
「主题」B01丨风景不殊——魏晋时代的文学与抒情
「主题」B02-B03丨从魏晋到晚明:寻找被压抑的抒情之声
「主题」B04-B05丨制造陶渊明:韵律、玄思与美酒打造的文学风度
「经济」B06-B07丨经济学仅仅是富人的学问吗?
「主题」B08丨谢灵运一生放纵不羁爱山水
采写丨袁春希
变革与离乱的朝代,也常常是文辞烂漫,郁结的情绪一涌而出,诉诸于诗文与想象的年代。
魏晋南北朝与晚明,正是两个极其相似的时代。诗人把道德选择、创伤记忆和家国之悲诉诸于笔下,在史籍中寥寥几笔的剧变,却是诗人一生的矛盾与伤痛。诗人既是记录者,也是含蓄而隐忍的演员。他们把自我隐藏在历史的幕布之下,通过意象与描写,把自我的命运剖白于千年之后的读者。因为在那时,优秀的诗人也常常是历史的亲身参与者。
庾信宫体诗中的“明镜圆花发。空房故怨多。几年留织女。还应听渡河”,写的何尝不是自己流离于南北宫廷之间的一生?钱谦益晚年的“望断关河非汉帜,吹残日月是胡笳”是否也是对自己忠贞与变节之间灰色的人生的一声无力的辩解?他们把自身的际遇融汇到风景、爱情与友情的描绘之中,诗歌承载了他们的历史记忆,也有着以情悟史的深切。
困厄与艰辛虽然使得诗人壮志难酬,但是也会激励他们,把创作当做时代的一声回响与心灵的报偿。中国历史不乏这样的时代与这样的人物,而他们为所留下,不仅仅是一卷诗书与穿越历史长廊的一声嗟叹,那些逃脱了礼教束缚的文字与狂风骤雨下的喘息与呢喃,既是他们对于历史与生命的声声嗟叹,也是时代狂潮下的辩解。
历史学家希冀于其中发现他们隐微的写作和隐喻,能否发掘出更多诠释和解读的空间。而文学家则敏锐地发掘出他们笔下的自我形象与情绪的流转,以及暗藏于诗文之间的自我反省与情绪流转。而这种山河易色之间的惨痛的生命经历,也让我们在书卷一端得以理解文学不可替代的意义——我们可以穿过时间、地域与语言的界限,移情于千年之前的古人。他们的遗民情怀与对于一个消逝的世界的怀恋与执着,在今天的读者与研究者的世界中得以还原与重现。他们化身为意象与典故,展开了一个独立于权力和现实的领地,供今天的人们抒怀与遨游。正如陈寅恪之于《柳如是别传》,赵园之于《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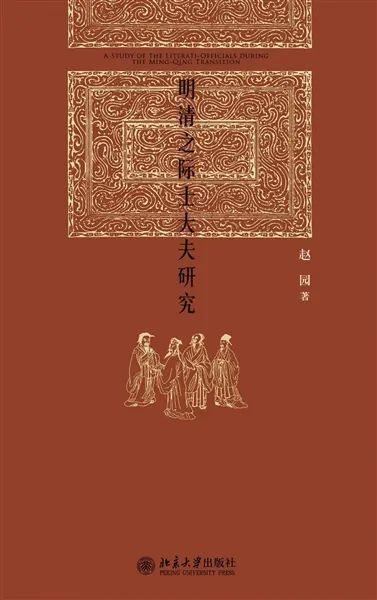
《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赵园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6月版。
曾任耶鲁大学东亚语言文学系系主任、著名荣休讲座教授孙康宜的研究作品《抒情与描写:六朝诗歌概论》《情与忠:陈子龙、柳如是诗词因缘》也正是对这魏晋与晚明两个衰世的一种展开与想象。历经了抗战、迁台、白色恐怖的孙康宜,把她的生命经验对照、倾注于陶渊明、谢灵运、陈子龙等诗人的作品之中。诗文的世界,既是她逃脱与隐逸的田园,也驱使她进一步思考中国文学的意义与结构。为什么往往在离散与困厄的时代,是诗人们尽其性情,写下惊天地泣鬼神之诗文的时代?而那些处于权力世界边缘的诗人,为什么往往会受到后世诗人的爱戴,成就了后来文学主流中的传统?
也许那些在现实世界中的失意与悲怀,会在文学的世界得到意外的补偿。也许礼教和仕途所遮蔽,会激发出压抑的性情和叛逆。那些幽微的诗学与意象,既是一声控诉与追问,也是隐匿于佛老与山水之间的逃逸。
魏晋与晚明:
中国历史中的“异类”
新京报:你研究的领域主要集中于魏晋南北朝与晚明两个时段,这两个时段有很多相似之处,比如山河鼎革的历史背景,思想上的不羁与解放,外来思潮对传统文化的冲击与改造等。对你而言,这两个时段最大的吸引力在哪里?这与你早年的人生经历是不是有一种对照与参考?
孙康宜:我觉得一定是有关系的。我博士主要是在高友工教授的指导下研究晚唐和北宋词的,但我在普林斯顿读博士时就对六朝文学感兴趣。我是读比较文学的,已故的耶鲁大学犹太裔教授埃里希·奥尔巴赫的《摹仿论》对我影响很大,他认为西方文学有两个传统,一是希腊传统,另一个是希伯来传统。这两种写法是不同的,一种是比较平行(paratactic)的,另外一种是渐进(hypotactic)的,这其实与中国文学的文体分类很类似。当我完成对晚唐词的研究去耶鲁教书之后,我就想着手进行六朝诗歌的研究。
我早年的经历确实对我的研究有很大影响,尤其是经过了抗战、迁台以及白色恐怖之后,很自然地我会移情于魏晋时代诗人们的生命经验。后来我写鲍照、谢朓尤其是庾信的时候,我就会想起人生中的伤心往事以及种种执念。我不是学究型的学者,我喜欢把我的生命经验与学问结合起来。在耶鲁时,余英时先生是我的同事,当时他的论文《名教思想与魏晋士风的演变》就阐述了魏晋时代对中国文化的突破性,他的研究对我有很多启发。所以我从陶渊明开始入手,以比较的方式论述陶渊明和谢灵运两个人。
我的研究与当时的文学批评是同步的,耶鲁一直是美国文学批评的最前线,当时流行描写(Description)与抒情(Lyric)两种视角的分析。后来我想,这两种视角也许可以对中国文化进行审视,因为陶渊明和谢灵运都属于抒情和描写并重的类型。对魏晋文学的研究,也与我受到杜甫的影响有关,杜甫对庾信的评价最高,他的“庾信平生最萧瑟,暮年诗赋动江关”是他暮年的感慨,在某种程度上,杜甫可以感受庾信的生命经验。我后来对明清文学与陈子龙的兴趣也是源自于此。
《情与忠:陈子龙、柳如是诗词因缘》的英文名叫The Late-Ming Poet Ch'en Tzu-Lung:Crises of Love and Loyalism,我对危机型的时代有兴趣,因为往往这种时代才能看出人的精神本质。陈子龙不愿降清最后投水自尽,在后世的研究者看来,他属于民族英雄,他的人格与诗文影响深远。他去世之后,为了逃避清廷的追捕,他的朋友纷纷噤声。到了十八世纪,乾隆皇帝为了表彰忠义反而追谥陈子龙为“忠裕”。和陈子龙相比,另一位晚明的大诗人钱谦益则备受冷落与抨击。清军攻陷南京后,他本想自尽殉国,但是借口“水太凉”,做了清朝的官员。这使得他与柳如是的关系一度坠入冰点。但是根据历史学者的研究,即便是降清之后,钱谦益依然在暗中资助与帮助南明抗清的义军。陈寅恪先生的《柳如是别传》对我也有着非常深的影响。

我每次的研究都与文学批评有关。因为我课堂上的对象都是美国学生(尤其是本科生),我必须用他们的语言让他们了解,所以我借助了奥尔巴赫的理论。奥尔巴赫所谓的“圣经传统”里,有一个重要的观点是指喻,《旧约》中往往预告了《新约》中即将出现的内容。后来我发现陈子龙在诗词中有很多相似的用法,他往往用自己的早年爱情诗中的意象来指涉、隐喻作为晚年的爱国诗。比如他在晚年也喜欢运用相思、清泪、雨打风吹等意象。我后来在他的作品中发现了很多对照,这个发现就成为我研究中的重要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