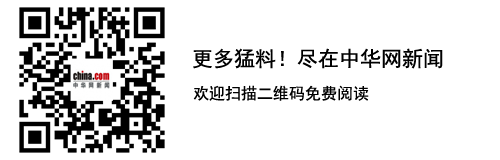一位新华社记者与温州改革的风云际会
温州,地处东海之滨。四十年改革的大潮拍打着绵长的海岸,开放的热风席卷着神奇的大地而蜚声海内外。作为记者的我与她风雨同舟35年,以400多万的文字忠实地记录了这个中国改革“风向标”的足迹。
1998年和2008年,正值中国改革20年、30年之际,我先后两次被破例推举为“温州改革开放十大风云人物”候选人,获评理由是:20年来,温州的改革与新闻报道息息相关,张和平对此立下汗马功劳。
我为之汗颜。
“中国第一座农民城”报道“第一人”
1974年冬的一天,我经过温州下辖的瑞安、苍南两县交通咽喉地带的龙港方岩下,举目眺望,四野民生凋敝,荒凉萧条。夜晚寄宿时听到一首凄凉的民谣:“方岩下,方岩下,只有人走过,没有人留下。”心头平添一丝悲凉。
10年后的冬天,方岩下“忽然一夜春风来”,唱出了“春天的故事”。1983年10月,龙港镇委书记陈定模带领一班人敢为天下先,顺应农民愿望,大胆突破禁区实行农村土地、户籍改革,允许土地有偿使用,允许农民离土离乡,自理口粮进城落户,允许自筹资金到龙港买地、建房。
一石激起千层浪。龙港方岩下及周边先富起来的农民纷纷从田地里拔出“泥腿”,怀揣“城市梦”,像19世纪大批华人涌入美国旧金山淘金一样,潮水般涌入白纸般的龙港,开全国之先河,大兴土木,掀起一场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农民自费“造城运动”。
仅仅两年工夫,这片杂草丛生的5个小渔村神奇般崛起“中国第一座农民城”,成为中国改革的一颗耀眼的新星。
但是,说归说、做归做。要不要、敢不敢在主流媒体报道这个改革当头、突破一系列禁区的新生事物,许多人心中没谱,不太敢冒这个险。
我时任浙江日报温州记者站主要负责人。职业的敏感性和改革嗅觉强力驱动我要“敢吃第一口”。1985年6月间,我与同仁沈胜良合作,在报社领导的有力支持下,以《苍南县崛起一座“农民城”》为题,用5000多字的超大篇幅在《浙江日报》首次报道了龙港农民城的崛起。这样的报道规格在当时实不多见。由此,龙港名声不胫而走。“破冰之作”也产生“邻里效应”,许多外省媒体纷纷跟进。
在尔后的几年里,我在《浙江日报》不断跟踪报道龙港的新气象、新面貌。《科技兴“城”看龙港》《“农民城”新风: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等多视角的报道向外界打开龙港另一扇“窗”,我成为《浙江日报》报道龙港改革的“首席记者”。
1992年我调入新华社,此后的10多年间,单独或与朱国贤、焦然、胡宏伟等同仁合作,在新华社、《瞭望》周刊、《浙江经济报》持续、深入报道农民城改革的新风貌、新经验:《“农民城”里无“农民”》《中国农民城为何能建成?》《“农民城”里观“农民”》《温州农民闯市场》《农民造城——龙港的奇迹》《现代都市不是梦——中国首座“农民城”听潮》《万国权赞扬龙港农民走出一条农村现代化路子》《中国第一座农民城的成功之路》等等。这些报道使龙港的改革形象进入全国层面。
中国小城镇改革的“催生剂”
1994年,龙港10年改革已取得了惊人的成就。这个原先只有8000人的5个小渔村迅速成长为温州南部地区工业重镇,成为遐迩闻名、颇具工业、商业、城市服务功能现代化雏形的新型城镇。
新的问题伴随而来,龙港陷入了“成长的烦恼”:鱼儿大了,鱼塘小了。
龙港向何处去?我敏感地抓住这个新问题开展深度调研。那阵子,我听到最强烈的呼声是:撤镇建市。即龙港与一江之隔的平阳县重镇鳌江镇合并建市。时任龙港镇镇长李琪铁对我说,从经济发展的总体规模、综合实力,以及城镇基础设施等条件衡量,龙港已达到国家规定的县级市的标准。但龙港现有的镇级经济、行政体制的格局与经济发展发生日益尖锐的冲突,使龙港镇经济社会发展陷入“小马拉大车”的困境。苍南县县长施德金也直截了当地对我说,龙港已到了非撤镇建市不可的地步。经过深入采访,我认为这个建市呼声顺应了时代潮流,代表了龙港未来的方向,对全国小城镇发展具有较强的指导意义。
但也有观点认为这件事很敏感,担心撤镇建市划出两个重镇等于割掉两个县的“精腿肉”,可能引起两县的混乱。因此,有关人士叫我勿“添乱”。
我坚持自己的判断。1995年1月初,我邀请时任总社农口报道编辑到龙港调研。1月26日我们发出供高层参阅的参考报道:《温州龙港镇陷入小马拉大车的困境 有关专家建议国家支持农民自费建市》。
稿件介绍了龙港已成长为城镇“小巨人”的现状,反映龙港陷入小马拉大车的窘境、镇级“小鱼塘”的功能和生态环境在城市规划、经济发展、工商税务金融交通管理等方面严重限制“鱼儿”生长壮大,反映干部群众希望改革上层建筑的呼声。稿子鲜明地提出:“专家建议国家继续尊重农民的发展愿望,顺应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运用政策发挥农民的创造精神,给龙港以县级市的行政建制。”
稿子对龙港建市模式作了前瞻性的勾勒:“专家还建议,在龙港农民自费建市的改革中,机构设置不要走传统老路,应该不要国家投资,精简行政机构,强化民间自治管理,建设小政府大社会的新型城市体制。”
有关专家称,农村城市化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之一,龙港是中国现代化新型小城镇的代表,这篇参考报道敏锐而及时地抓住了中国第一座农民城发展中的一个新问题,深刻反映了中国农村小城镇上层建筑严重制约经济基础的新矛盾,建设性地勾勒了未来现代化新型小城镇发展的新架构、新模式,为中央提供了重要的决策参考,这对中国农村改革、进一步推进小城镇城市化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稿子犹如催生剂,“催”出龙港走向城市化的重大机会。中央有关领导同志在报道上作出重要批示,主要精神是:今后这类小城镇将可能大批产生,新型的小城镇应是新体制、小政府大社会,高效率,清正廉洁的机构。
根据中央领导这一重要指示精神,国家体改委立即开展全国小城镇改革重大课题的研究。随之国家启动了这项重大改革工程,成立了全国小城镇综合改革领导小组。随后,国家体改委与建设部、公安部、国家计委、民政部等11个部委联合颁发《关于小城镇综合改革试点指导意见》,制定出改革试点实施方案,决定在全国实施改革试点,以龙港镇为首的57个城镇名列其中,改革试点为期5年。专家称,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实施小城镇综合改革,在中国小城镇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由此,龙港在行政、财政、计划、户籍、工业、城建、教育等7个方面的管理体制进行大力度的改革。比如,在许多领域赋予县级经济管理权限,建立浙江省第一个镇级金库,实行县级计划单列,统一规划、征地、建设小城镇,允许农民进城落户等。总之“给权给人给钱”,“事权财权人权”同步标配。
这项改革为龙港插上腾飞的翅膀。经过5年的改革,龙港创建了印刷工业园、小微创业园等10个工业园区,总面积8.55平方公里。建成国家级的“中国印刷城”“中国礼品城”“中国台挂历集散中心”“中国印刷材料交易中心”,实现了从“农民城”向“产业城”的跨越。
时任苍南县委常委、龙港镇委书记黄宗克形象地说,经过改革,龙港发生了三大显著变化:农民→居民→市民;农业社会→工业社会→现代社会(雏形);小农村→小城镇→小城市。
这轮改革也为龙港后续改革产生了强大的“后坐力”。2014年12月29日,国家发改委等11个部委联合发文《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改革试点方案》,国家实施新一轮的新型城镇化综合改革,龙港被列为试点镇,借以为全国提供借鉴和复制样本。
温州金改的“助产士”
2012年3月28日,对温州来说是一个非凡的日子。这一天,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设立全国唯一的温州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
鲜为人知的是,这项重大的金改与新华社的一篇参考报道紧密相关。
那是2011年上半年,温州坊间频频传出一些不祥之兆:江南皮革公司、三旗集团、波特曼餐饮公司、浙江天石电子公司等4家知名企业相继倒闭、老板“跑路”(失联、潜逃)。这犹如小霹雳在温州引起不小的震动。这些红红火火的企业到底怎么啦?它们的重创意味着什么?到了7、8月间,情况更不妙,又有不少企业紧随其后,致使大批员工失业。
我大脑的弦绷紧起来。经调查发现了其中的“奥秘”:2011年初,国家收缩信贷规模,银行贷款资金大量减少,“银行变成没钱的穷人”。许多中小企业遭遇“钱荒”,银行的利率变相拉高。“官钱”一断,民资成了“香饽饽”,民间借贷因之暗流汹涌,借贷利率“水涨船高”。
企业无法从银行续贷资金,巨额的民间“过桥”借款资金和高额的利息如同两把利剑刺入企业的心脏,最终导致资金链崩断。一些老板被逼上绝路选择“跑路”,一些人因绝望而跳楼、跳河。企业因之倒闭,员工无家可归。严峻的局势表明温州密集性爆发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民间债务危机。
我意识到这是一个相当严重的问题。新闻敏感、责任感和使命感“指令”我马上“动起来”!
抢时间迅速发稿迫在眉睫,但苦恼的是,我虽了解到几例老板跳楼的个案,但整体情况难以掌握。焦急之中,我抱着侥幸的心理给一位银行副行长打电话。“踏破铁鞋无觅处,来得全不费功夫”,他是个知情人,出于对我高度信任,他不怕压力和风险,对我和盘托出内情。
我估计这篇“猛料”发出来,有人肯定会给我施压。对此,我义无反顾地选择了新华社记者的职责、良知和使命。
9月27日,我在总社有关领导和编辑的支持、指导下,发出第一枚“重磅炸弹”《温州民间借贷崩盘引发多起老板跳楼事件,一周内2死1伤》。稿件反映了温州触目惊心的金融“灾情”和走势:严峻局面已造成社会人心惶惶。各界人士担忧,元旦、春节资金回收的高峰期到来时,将可能发生“地震”,出现更严重的“跑路”、倒闭、挤兑、跳楼、员工拦路、黑社会暴力、绑架等恶性事件。
9月28日,我发出第二篇参考报道《温州民间借贷迫近“崩盘”,民企老板“跑路”呈高发态势》。稿子反映了百乐家电公司、温州奥米流体设备公司等至少有80多家企业老板“跑路”、企业倒闭的严重事件。并点出这只是已浮出水面的,在“水下”暗流涌动的起码有数百家小企业,倒闭企业欠款超100亿元,目前涉及民间借贷纠纷的金额达9.31亿元,并在不断“刷新”。
为了提供完整、有价值的决策参考,我在“报灾”“报果”的同时也“报因”:今年以来在国家货币紧缩政策的深度影响下,温州中小企业普遍遭受“三荒两高”严重困境。在市场高物价、银行负利息、股市持续低迷、楼市深度调控、投资渠道步步收窄的多重“夹击”下,民资殷实的温州民间借贷变得异常活跃,甚至从炒房、炒矿转向“炒钱”。这导致民间借贷利率一路飙升,月利率普遍已高达3分左右,甚至5分、1毛。“5分利”等于资金的年回报率是60%,相当于一般制造业年利润率的6倍。如此离谱的超高利润率匪夷所思。
针对众多企业感到当前遇到的困难比金融危机更严重,有专家提醒,温州这种情况可能会演变成类似美国的“次贷危机”。知名财经评论员叶檀认为:“如今实体经济资金池紧缩得就像大旱期间的鳄鱼池一般”。
稿子更要报“策”:温州市委希望中央采取积极有效措施和对策,诸如支持利率市场化改革、增加小额贷款公司的总数等,以有力支持实体经济和化解危机。
9月30日,我连珠炮似的发出第三篇稿,反映温州市政府为遏制危机扩大蔓延而积极“救火”“救灾”的紧急行动,同时进一步反映温州要求国家支持实施金融改革的迫切呼声。
这组3篇参考报道当即引起国务院高度重视。2012年3月28日,国务院决定在温州设立全国首个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
几天后,浙江省委省政府在温州部署金融改革。温州市金融部门的同志坦率地说,温州金改走的是“自上而下”的程序,这才有这么好、这么快的结果。如果按常规流程一级级、一层层向上报批,建立温州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简直比登天还难。
鉴于这组参考报道对温州金改起到的重要作用,被评为新华社社级好稿。
温州金改实施后,我更是没歇着。多年来,我通过公开、内部报道不断反映温州金改的新气象、新问题。
2017年金改5周年之际,我虽已“退出江湖”近2年,责任感驱使我“再作冯妇”。我与同事王俊禄合作,以《温州金融改革五周年:修复“温州信用”溢出“金改红利”》为题,重点反映金改三大成果亮点和可借之鉴:推进民间资本走向“阳光平台”、为中小企业“通脉活血”、倾力修复“信用破产”堤坝。2017年4月,该长篇报道分别通过新华社内部稿和公开稿发出。
2017年4月20日,浙江省委主要负责同志在这篇新华社内部稿上批示:温州市要坚持金融改革不动摇,且不断深化,以取得更好成效。
温州市金融办副主任余谦说,批示犹如给“降温”的温州金改添了一把“大火”,金改火焰再度燃烧起来。此后,浙江省党代会、省人大报告和省经济工作会议都明确要深化温州金改。特别是针对温州5年金改的1.0版,根据省委省政府的部署,温州制定了“金改2.0”版方案,将之推向更高的台阶。“温州金改继续在路上!”余谦满怀信心地说。(特约撰稿张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