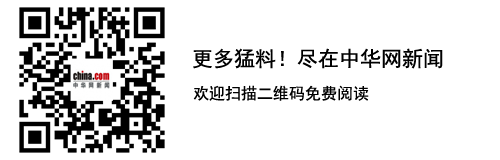崔晓柏: 撞见历史 有话要说(2)
“我当年是度过了一个非常贫瘠的青春期,那时整个朝阳地区在画画领域连一个石膏像都没有,我们就是照着人直接画,就这么画出来了。我们到工厂去,画工人,到农村去,画农民。最长的一次是走了几个月,我们背着画具一个村子一个村子走。我们就是普通人家的孩子,因为热爱走上了绘画这条路。”
“我在朝阳艺术馆工作的时候,办公地点就在朝阳最大的寺庙佑顺寺,艺术馆、博物馆、图书馆,三个馆在一块,统称三馆。当时我在那里住独身宿舍,每天早上外出写生,回来之后在院里总能碰见一个考古学家,他穿着对襟褂,洗得干干净净,灰色的,当时院里有一棵树,下面有一张破藤椅,有一张破桌,摆的全是书,线装的,文献类的,他每天就窝在那里看书。他每次看见我都打招呼,特别客气。我一直不知道他为什么那么谦恭,过了60岁我才知道,他是在向未来致敬。当年我在不经意当中,接触了很多这样的人。”
“当年朝阳地区考古挖掘出来的青铜器等,就放在回廊下,用大筐装着,上面有编号。我们打开窗户从中拿出来一件,就照着画画,完了之后再放回去,每天就盯着那些东西,没完没了地画下去,从来也不问那些器物是什么,只是认为这个器物好看,如何把它的颜色形状表达出来。那段时间的浸染,实际上对后来的艺术道路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在后来的路上,不停地遇到它们,不停地与历史相撞,那些东西开始有用起来,它活了。”
“严格意义上讲,我不是一个经过专业训练的画家。恢复高考的时候,我想报考鲁美,可是连准考证都拿不到,后来有一个机会,1980年,鲁美的油画研修班在辽宁要招十几个人,要求在职干部,我报名参加了这个考试,这个考试特别有意思,没有考石膏像,考的是画模特,他们认为画模特儿很难,我是野路子,专画那个出身,最不怕画这个。就这样,我考上了鲁美的干部专修班。那时候的教学资源匮乏,我到鲁美就是反复翻图书馆那些画册,一本一本的临画册。那个阶段我主要就是开了眼界,之后就留在了沈阳工作,1981年,在省委的《理论与实践》杂志社当了一名美编,只待了一年。我心里还是想着要画点画,1982年,调到了团省委办的《新少年》杂志当美编。在那里我工作了十年,这十年是我一生当中最安稳的日子。我努力的画插图、画连环画。在那段日子里,我结婚了,我30岁了,有了自己的房子,有了自己的孩子,有了自己的家,有了自己的事业。”
相关新闻
从历史最差到历史最佳,中国冰壶男队斩获世界杯亚军
原标题:从历史最差到历史最佳,中国冰壶男队斩获世界杯亚军一个月以前的冰壶世锦赛,中国冰壶男队仅仅取得了2胜10负,创造了历史最差成绩,在加拿大莱斯布里奇留下了他们落寞的背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