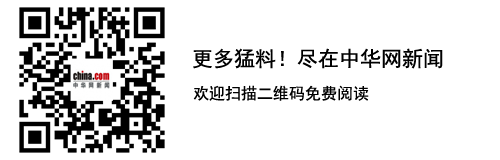诺奖得主石黑一雄也写奇幻小说 如今住在一个小村庄里

编者按:瑞典斯德哥尔摩当地时间2017年10月5日下午1点,瑞典学院将2017年度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了日裔英国作家石黑一雄。他的上一部小说是带有奇幻性质的《被埋葬的巨人》,小说中文版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虽然与奈保尔、拉什迪并称为英国文坛“移民三雄”,石黑一雄的写作其实并不“移民”,他也是因为反感批评家对其文化身份过度阐释,才以《长日留痕》告诉英国文坛,我也可以把英国写得这样好。
中世纪的英国平原,是诗歌温床和文学沃土
2015年3月,贝塔斯曼旗下的克诺夫出版社(Alfred A.Knopf)发布了石黑一雄久违十年的新作《被埋葬的巨人》。这家出版社出版了他自《长日留痕》以降的所有作品,也见证了作家一次又一次在题材上的跳跃:1989年出版的《长日留痕》,讲述了一位英国管家在二战后回忆自己在战时的职责与恋情;1995年的《无可慰藉》,追随一位知名钢琴家在欧洲小镇进行演出的诡谲经历;5年后的《上海孤儿》书如其名,讲述一名英国侦探调查在上海度过的童年发生的一场疑案;2005年,大受好评的《别让我走》又跳到了1990年代的英国,聚焦一个培养克隆人的教育机构里少男少女追寻身世之谜的故事。
这一次,石黑一雄选择了中世纪的英国平原,时值不列颠人和撒克逊人兵戈相向的动荡关头,有战火、精灵还有作恶的巨龙。
这里是英国诗歌的温床,前有开天辟地的《贝奥武夫》,后有埃德蒙·斯宾塞(Edmund Spenser)的《仙后》(The Faerie Queene),这里也是J.R.R.托尔金的文学沃土。这里盛产战火、死亡、爱情和英雄,犹如河畔丛石间肥美的鱼卵,万物有灵,但凡有形体的似乎都能说话,它们问,石黑一雄,你这个陌生人,你在这里想要得到什么?
他解释道,十多年以来,他一直想写一个探究集体记忆的故事,关于社会和文化如何通过失忆的方式,从历史的暴行中振作过来。他想到了二战后的法国、当代美国或日本,又担心“写实的历史笔法会削弱主题的效果,让它过于狭窄”(他的前三本小说便遭遇历史、文化角度的过度阐释)。
出于“去政治化”的目的,他开始寻找一个更抽象也更抽离当代的背景,这时他读到一首写于14世纪的骑士诗歌《高文爵士与绿衣骑士》(Sir Gawain and the Green Knight),讲述了亚瑟时代的英国。
“我对亚瑟王、戴尖帽子的女人们之类的题材并不感兴趣,但我觉得这种荒芜诡谲、文明尚未诞生的英国可能会相当有意思。”石黑一雄说。
这的确不是一个关于亚瑟王的故事,主人公是一对年迈的夫妇阿克塞尔和比阿特丽斯,他们和其他不列颠人一同生活在一个山村里。整座村庄乃至村庄之外的大地上空都弥漫着一层迷雾,这片迷雾带走了人们的记忆,他们像梦中人一样生活行走,却忘记了生活的来龙去脉。阿克塞尔和比阿特丽斯也不例外。
有一天,他们突然想起自己在邻村还有一个儿子,于是决定出发去寻找他。在路上他们结识了新的旅伴——撒克逊战士威斯坦和他不久前救下的男孩埃德温;四人又遇到了已故亚瑟王的侄子高文爵士。他们在高文爵士的庇护下化险为夷,最终找到了迷雾的源头。

《被埋葬的巨人》书中插图。
石黑一雄向妻子征询新书的书名,最终,他们一同发现了一个合适的意象,隐隐指涉被深埋于脑后的痛苦记忆。
“埋得很深的巨人现在要动起来了,”石黑一雄说,“当他醒过来时,将会有一场大难。”
比阿特丽斯提到,丈夫先她一步渡河进入神秘国度后,她遇到一位老妇,而她必须向船夫证明她与丈夫的爱情完美纯粹,不夹杂任何苦涩、嫉妒或羞愧——唯有如此,她才能够乘上小舟抵达彼岸。这让比阿特丽斯沉思:当你甚至无法记起和丈夫共度的过去时,你们又该如何证明彼此的爱情呢?
记忆是宝贵的,它是个体存在的不二证明。正如比阿特丽斯对阿克塞尔所说:“如果这是你所记得的,阿克塞尔,那就当它是这样吧。如今我们面对这一片迷雾,任何记忆都是宝贵的,我们最好紧紧抓住它。”
作家通往伟大的门票是他发现的母题。记忆是石黑一雄的母题。他努力用七本小说敲打记忆的方方面面,就好比为水做一尊雕像。而到了《被埋葬的巨人》中,问号再一次执着地悬挂在空中,最后变成石黑一雄最擅长的一种氛围,一个淡影,一种无可慰藉的心情。直到最后一章,读者才会明白阿克塞尔和比阿特丽斯究竟是何许人也,他们的儿子发生了什么事,以及,如果他们恢复了记忆,他们是否还真爱着对方。
然而这正是石黑一雄小说的魅力所在。迷雾笼罩住龙的真身,我们只能凭借云层间的一鳞半爪勉强拼出一个原貌。这样的小说结构尽可能延长了推理的时间,也让重读更富趣味。
评论界毁誉参半
这一次,坚持不懈地打破自己文学疆界的石黑一雄,似乎有些在意读者和学界的反响。“我不知道会发生些什么,”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他说道,“读者会跟随我进入故事吗?他们会理解我在做的事,还是因为表层的元素而产生偏见?他们会认为这是本奇幻小说吗?”
就目前而言,文学界对这本新作的反应是毁誉参半的。
美国书评杂志《科克斯评论》(Kirkus Reviews)认为,这本书展开了一场“通往英国民间传说的迷雾的抒情之旅……一整个国度的住民在失忆中寻求意义,这一设定非常迷人……一个成人童话,对一种丰茂文学传统的继承与发扬。”也有评论家认为,小说虽然情节推进缓慢,但行文内敛精确,读起来轻松,但释卷难忘。
不过,《纽约时报》的评论家角谷美智子认为,“石黑一雄摈弃了两部杰作《长日留痕》和《别让我走》中的特质——精准、含蓄、曲折——转而投向寓言式的原始主义,阻碍了他的禀赋才能。”
让角谷感到生硬的奇幻元素,却让奇幻文学粉丝们称赞《被埋葬的巨人》不仅对石黑一雄而言是一个飞跃,对奇幻文学这一文学类型同样也是向前一大步。《纽约时报》还采访到了《云图》作者大卫·米切尔,后者慷慨地说,如果要拿刀逼着他选一本最喜欢的石黑一雄的作品,他会选《被埋葬的巨人》,因为它以奇幻为渠道探索诸如爱和死亡的问题。
“奇幻与文学的结合可以达到单纯的现实主义作品所不能达到的效果……对小说中的物理现实法则进行一点扭曲,并不一定意味着小说就变成‘快点!傍晚之前森林就会涌入无数半兽人’之类的故事了。”米切尔补充道。
这并不是石黑一雄第一次尝试让类型与文学结合。带有历史小说痕迹的《长日留痕》,侦探小说噱头的《上海孤儿》乃至科幻小说色彩的《别让我走》一次又一次向读者证明,这是一个善用“迷思”(myth,意指神话、故事)的高手。他写的英国比英国还英国,他能让读者中的老管家们提笔写信,感谢他对这个行业的忠实描述。他的作品的仿真效果堪比好莱坞制作,投身到他的故事里,如同纵身跃入某个制作精良的游戏,替换游戏设定对实质并无伤筋动骨的损害。仿真的技能成就了他的写作,也阻碍了他的写作。
作家步入老年,他说“常见的一条路是衰退”
石黑一雄如今住在一个小村庄里,除了散步和喝下午茶,似乎并无别的娱乐方式。“理论上,这是写作的至佳宝地,但有些地方就是太漂亮了;实际上,它只是个喝茶吃蛋糕的好地方。” 在《无可慰藉》中我们看到了一点石黑一雄的生活:作为作家,常年周游各地宣传新书、接受采访、乖乖交出自己的时间表……也唯有在《无可慰藉》中,我们借主人公莱德的疲惫,看到了石黑一雄的疲惫,也看见了我们的疲惫。但是《无可慰藉》是罕见的,石黑一雄很快又藏起来了。
大部分时候,他的仿真并不涉及自己的当代生活。电影、书籍是他仿真的源头。他在过去的访谈中承认自己写《远山淡影》时借鉴了日本武士电影,也早有批评家深入探讨石黑一雄作品中的亚洲电影元素。只有《浮世画家》中那座宅邸是真的——少年时代的石黑一雄曾经亲眼见过,然而自那以后,他再也没有写过关于日本的长篇小说。
石黑一雄终究还是遇到了所有作家在老年遇到的问题:在记忆渐渐褪去,阅历压弯背脊的冬季,应该走向哪里?为了寻找答案,他翻开菲利普·罗斯的浓缩、含蓄的小说《复仇女神》(Nemesis)和科马克·麦卡锡的反乌托邦小说《路》(The Road);同时也听鲍伯·迪伦的晚期作品,那种温暖、丰茂的风格是另一条蹊径。
他的妻子说,“你最后会选哪条路呢,真有意思。”
“常见的一条路是衰退。”他回答。
然而或许他不会衰退,而只是一直沿着一条水平线滑行。
他渴望抵达一种普世的广域写作,让每一个人在书中读到自己,因此他在挑选故事背景时那么刻意地用力地“去历史化”“去社会化”“去私人化”,尽管他的前六部小说都是第一人称,我们对作家本人的观点还是了解地那么少。他故事里的迷雾隔离了他和读者,也隔离了小说与当代生活的距离。他的小说里没有福楼拜式或曹雪芹式在后世不断轮回重生的艾玛、夏尔、贾宝玉、刘姥姥,只有石黑一雄式的缄默内敛、如同英国天气一般、如同黑泽明武士电影一般的叙述者,欲说还休。

《被埋葬的巨人》英文书封。
相关新闻
北京通州:诺贝尔奖得主可获100平米人才公寓租金减免
5月21日,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政府发布《关于开展2019年度通州区人才公寓配租工作的通知》。此次人才公寓配租,符合条件的诺贝尔奖、图灵奖、菲尔兹奖等国际大奖获得者,中国科学院院士和中国工程院院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