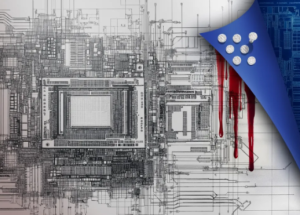调查丨租地种田的家庭农场,该如何“传家”?
3月底,吴瑞瑞位于安徽蚌埠的600多亩小麦,高度基本上都没过小腿了,去年的秋汛对这里的影响不大,小麦长势不错。今年,吴瑞瑞又多租了几块地,价格比往年都高,夫妻俩的压力也更大了。在黑龙江哈尔滨,苗加上租的5000多亩地,正在进行春耕前的准备,今年的地租涨了100元,每亩租金达到了1100元。
3月25日,农业农村部发布《关于实施新型农业经济主体提升行动的通知》,鼓励有长期稳定务农意愿的农户适度扩大经营规模,成长为“家庭农场”。并在将来为家庭农场统一赋码,提供产品销售、品牌推广、贷款保险等提供便利服务。
到2021年,全国家庭农场数量已经超过390万家,他们大多像吴瑞瑞一样,以家庭为单位,通过流转土地实现规模经营。然而,在快速发展的同时,这些家庭农场,也面临着土地不稳定、风险不确定、成本过高等种种困境。专家指出,“让真正种地的人得到土地,家庭农场才能更好地发展。”

黑龙江哈尔滨,进入4月,苗加上的农场里开始整地备耕,资料图片。新京报记者王颖摄
“租地种田太不稳定了”
家庭农场并非中国本土的产物,而是农业现代化之后的舶来品。最早开始研究家庭农场的中国农业大学教授朱启臻介绍,改革开放以后,逐渐有了一些承包大户,在实践中渐渐形成了几个特点,第一是家庭劳动力为主,区别于雇工农场,第二是适度规模,区别于传统小农户,第三是农业为主业,主要收入来源于农业,区别于兼业农民,第四是稳定性,可以实现代际继承,区别于短期承租。
“改革开放后,家庭农场这个词就一直在用,但真正写入中央文件是在2013年,最近几年,作为新型经营主体,已经引起了广泛的重视,多次出现在中央文件中。”朱启臻说。
吴瑞瑞家的地是夫妻一起打理,最接近家庭农场定义的经营者案例,但和真正的家庭农场仍有距离,最关键的问题还是土地。“稳定性是基础,土地承包关系长久不变是基本条件,唯有长久不变,才能给农民以长远预期,农业经验和对土地的感情才能形成,并在代际之间传承。”朱启臻说。

4月1日,吴瑞瑞在农场里进行飞防作业。受访者供图
但稳定性,恰恰是吴瑞瑞他们所面临的最大困境,吴瑞瑞的600多亩地,分散在几个不同的村庄,都是零散的地块,而且时常有变动。“有的刚租几年,忽然就不给租了,刚种熟的地,又不能种了,只能再找地方。”他说。
“太不稳定了”,位于河北省邯郸市的郝科向说,他和父亲、妻子、儿子一起租地种粮,目前有1300亩地,种了十多年,经历了太多波折,“1300多亩,都是从农民手里,一小块一小块租来的,有些能连成片,但经常有一家人或者几家人忽然不租了,因为别人给的价格更高,最多的一次,300多亩地说不租就不租了。”
同样租地种田的苗加上也告诉记者,他的农场在黑龙江哈尔滨,现在有大约5000亩地是每年一签合同,没有农户愿意签长期合约,“因为租金每年都在涨,2019年的时候,一亩地还是400元,2020年涨到了600元,2021年1000元,今年1100元。这个价格,实际上已经没什么利润空间了。”
“最怕的就是游资进来”
对家庭农场的经营者来说,不稳定的土地关系,带来了高昂的成本。
“有时候,合同也没用,说不租就不租,还没法儿追究对方的违约责任。”郝科向说。郝科向在河北邯郸种地,他告诉记者,今年最高的租金已经达到1050元了,最低的也有800元。
“最怕的就是游资进来。”郝科向说,“这些年,经常有游资来租地种植,他们不懂农业,也不了解农业的收益,愿意付出更高的价格流转土地。比如说忽然有一个企业,以比市场价高150元的价格租地,农民立刻就把地租给他们了,我们跟不跟呢?不跟没地可种,跟了赔钱,游资赚不到钱,第二年就走了,可价格却下不来了。”
十多年的种地生涯中,郝科向经历最多的,就是不可预知的价格,这让他不敢在土地上投入资金。“比如打井,打一眼井,除了政府补贴之外,自己还要掏1万多元。但有时候,刚打好井,农民忽然就不租给你了,等于白投入,也没办法追回投资。”郝科向说,他经历过三次同样的事情,三眼井白白给别人打了,“一点儿办法都没有。”
即便要投资,也缺乏资金来源,苗加上告诉记者,“流转的土地,肯定不能作为抵押物,对农民来说,农机、房子也不能抵押,只能通过信用贷款获得小额资金,远远不够改造土地的投入。事实上,因为地不是自己的,也没法儿投入过多的资金去改造。”
家庭农场如何“传家”
“土地不稳定,是家庭农场发展最大的难题,也是制度瓶颈。”朱启臻说。“家庭农场面临的困境,是很多因素造成的,比如认识问题,有些基层的管理者,不懂什么叫家庭农场,一味地追求大户引入资本,结果经营情况并不好,反而扰乱了市场。还有的地方,把土地收回来,划成规模化的地块,5年一承包,认为这就是家庭农场,其实也不是。”
土地的不稳定,给家庭农场的经营者带来了高昂的成本,也间接助推了短期行为的普遍化,“不能稳定获得土地的经营权,谁会真正去保护土地,在土地上投入呢?”朱启臻说。
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着重强调,“坚持农民的主体地位”,朱启臻认为,这也是为家庭农场这样的新兴经营主体提供了保障,“家庭农场和其他的农场、商业化种植不一样,是农民自己为自己劳动。”朱启臻说,“都说农民是土地的保护神,事实上,只有在家庭农场的环境下,才最容易实现。无论是藏粮于地,还是藏粮于技,家庭农场都是最有效的实现路径。”
只是,这条路还不够畅通和平坦,“其实,不管是中央文件,还是各种政策,都是非常好的,对家庭农场的发展很有帮助,但在具体的执行中,有些还很难落实。主要还是观念问题,没有真正理解现代农业发展的机制。因此,在具体实施的时候,经营者只能通过流转获得不稳定的土地,面对不确定的未来。而事实上,理想的家庭农场,应该可以支撑起一个家庭长久的收入和生活,唯有如此,才能在土地上实现充分就业,才能让农业经营后继有人。如果都是小农户经营,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农业劳动自然后继乏人,以后谁来种地呢?”
“土地碎片化,劳动力短缺,农机成本很高,所以,没有年轻人愿意继续务农。”苗加上说,他的农场规模不算小,但他的孩子,也都不愿意继续从事农业。
相同的问题,郝科向也在考虑。目前,郝科向的儿子和他一起经营农场,但流转来的1300亩土地,并不能给儿子带来足够的吸引力,“他还是不想干农业,我自己也很难确定,这份事业能不能持续下去,”郝科向觉得,稳定和规模是一个家庭农场能否传递到下一代的基础,而其中,稳定尤其重要,却恰恰是最缺乏的。
“迫切需要建立土地退出机制”
“让真正种地的人得到土地,家庭农场才能更好地发展。”朱启臻说,而要实现这一点,最迫切的,是建立土地退出机制。
家庭农场不但需要适度的规模,也需要稳定的土地经营权,而短期租赁,显然无法实现。而要让愿意种地的人,获得更多的土地,并非不可能。几十年来,数以亿计的农民进入城市,大量劳动力离开土地,朱启臻认为,有条件建立土地退出机制,“当一个农民离开土地,有了稳定的非农收入,并被纳入到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中,又无力耕种土地时,就应该无偿退出耕地。”
朱启臻认为,进入老年的农民,也应该通过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等,建立土地退出机制,“老年或失去劳动能力的农民,通过社会保障体系获得了合适的保障,是可以退出土地的。”
此外,已有的退出机制,同样也可以达到“让种地的人得到土地”的目的。朱启臻介绍,“我国《土地管理法》中规定,耕地撂荒两年就可以收回,但在现实中,这一规定极少执行,更有一些地方,通过政府进行规模化流转后,却因为难以经营,而出现了规模化的撂荒,同样没有被收回。如果能够严格执行,这些撂荒的地,可以通过承包的形式,让愿意种地的人来承包。”
土地承包权的转变,是否和“三十年不变”的政策相悖?朱启臻认为并非如此,“土地承包三十年不变,是保护农民的利益,那些已经不再是农民,或者有了稳定的非农收入、纳入到社会和保障体系中的人,是可以退出的。比如说,我们的土地承包制度,是以家庭为单位的承包,如果一个家庭,全家人都已经进城了,有稳定收入,且有各种社会保障,他们是否可以退出呢?显然是可以的。而他们退出的土地,就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将承包权转给那些真正愿意种地的家庭。”
新京报记者周怀宗
推荐阅读

权威快报丨国家卫健委:时不我待落实各项防控措施
新华社微博2022-04-01 15:21:00
疫情当前,清明祭扫这些新方式可以有!
新华网2022-04-01 15:21:00
4月8日起 北京市郊铁路通密线列车开行时点调整
新京报2022-04-01 15:11:01
"幻影"战机坠海原因未明 台军方宣布今天全面复飞
新浪网2022-04-01 15:39:17
美国炮制恶劣谎言打压中国官员 中方宣布对等反制
北京日报2022-04-01 13:23:23
“杜鲁门”号航母将延长部署在地中海地区至夏季
央视网2022-04-01 15:04:59
韩国两军机相撞后坠毁致3死1伤 2名飞行员跳伞逃生
环球网2022-04-01 15:27:45
美国防部称曾多次试图与俄方接触 但未成功
海外网2022-04-01 15:02:59
日本考虑引入攻击无人机 或违反“专守防卫”原则
参考消息2022-04-01 14:23:47
澳大利亚宣布增加防务开支
参考消息2022-04-01 10:01:41
美媒文章:拜登新预算被批“重军轻民”
参考消息2022-04-01 14:25:14
中国油价处在世界什么水平?接近日澳但比美国还贵
驱动之家2022-04-01 10:53:35
上海病患求助遭拒:除颤仪能否外借 律师如此解读
人民网2022-04-01 13:44:27
博士8年未毕业送外卖给孩子治病:时间灵活不费脑
中国网2022-04-01 14:02:17
5岁男童幼儿园午睡时猝死 老师称失职正与家属沟通
搜狐2022-04-01 14:16:45
美航天局:感谢俄方将美国宇航员安全送回地球
海外网2022-04-01 14:41:09
果然!这次美国大片里苏-57“就是坏人”
环球网2022-04-01 10:11:02
车臣首领展示所缴武器并喊话拜登多送点 亲自奖励
东北网2022-04-01 15:15:43
深圳行程码“摘星” 提醒我们:抗疫是一场持久战
潇湘晨报2022-04-01 13:34:52
新毒株XE传播速度比奥密克戎BA.2快 已在英格兰传播
快科技2022-04-01 14:30:18
俄方称亚速营撤离直升机被击落
海外网2022-04-01 14:44:51
美国防部称:军队丑闻频发与领导层不作为关系密切
央视网2022-04-01 15:13:16
普京签令征召13.45万新兵!
环球网2022-04-01 11:00:50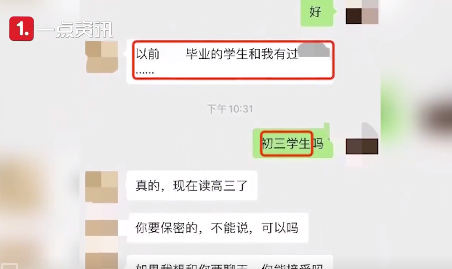
教师自称性侵多名学生 教育局回应部分属实已刑拘
中国网2022-04-01 14:47:42
全民免费的新冠疫苗有多赚钱?科兴盈利或超800亿
重庆晨报2022-04-01 09:47:47
俄乌战事的“意料之外”,有何启示?
参考消息2022-04-01 14:08:41
核酸点多人共用棉签采样?当地回应:演习不是实检
东北网2022-04-01 14:39:04
澳门连续15年向居民派钱 永久居民人均发1万澳门元
映象网2022-04-01 10:23:25
俄称乌军部署锚雷 威胁击沉试图离港的外国船只
海外网2022-04-01 14:53:13
神舟十三号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 正为4月返回做准备
央视网2022-04-01 14:32:51
南奥塞梯欲加入俄联邦 美国表态不会承认公投结果
环球网2022-04-01 09:53:24
德国拒绝俄方卢布结算天然气要求 坚持按照合同办
环球网2022-04-01 10:31:08
为抵制俄罗斯,拉脱维亚禁止展示字母“Z”和“V”
环球时报2022-04-01 15:09:53
乌外长喊话让印度说服俄方:利用俄印友好关系
环球时报2022-04-01 15:06:50
上海哮喘离世老人家属发声:相信医生还能做得更好
中国网2022-04-01 10:14: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