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什么时候,我们都需要幽默
作为人类的基本情感之一,有关笑的语言不一而足,古有“启颜”“霁颜”“笑逐颜开”,也有“讪”“诮”“哂”“嗤”;今有“哈哈”“呵呵”“嘻嘻”,也有“:-D”“XSWL”“笑yue了”及其衍生表情包。挪用一句经典的电影台词,那就是——笑,其实无处不在。
但当我们深入笑的意涵,不难发现的是,每一种笑所对应的情绪实际上复杂而微妙,它总是指向某些事件、事物、言谈与情境。事实上,笑很少是一种单纯的身体反应,更多时候,笑的背后藏着广阔的意义世界。这也难怪笑会成为自古至今各类学科所衷情的研究主题。

电影《爱情神话》中的知名幽默桥段。
那么,我们为何会笑?又为何而笑?这就要提到与笑有关的另一个概念:幽默。在《幽默》一书中,文化评论家伊格尔顿批判性地检视了深藏于幽默背后的精神分析机制以及幽默在几个世纪以来的社会和文化意涵演变。从霍布斯的“优越论”(supeiority theory),到弗洛伊德的“缓释论”(relief theory),再到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carnival theory),幽默时而是排解苦闷的万能药,时而是拉平一切的颠覆者。某种意义上,幽默的复杂性,正如人性。
最终,一个有趣的问题跃然纸上:剖析幽默会杀死幽默吗?对此,伊格尔顿给出的回答是:了解大肠的生理结构,并不妨碍享受美餐。
下文经出版社授权摘编自《幽默》一书的“论笑”一章,伊格尔顿分析了笑的不同形式及其背后复杂的意义系统。篇幅所限,内容较原文有较大幅度删减,小标题为编者所拟。
原文作者丨[英]特里·伊格尔顿
摘编|青青子

《幽默》,[英]特里·伊格尔顿著,吴文权译,后浪|中央编译出版社,2022年6月。
笑确乎自哭进化而来
笑无时不在,无处不在,种类繁多,不一而足。塞缪尔·约翰逊在《定义喜剧之困难》一文中称,人类智慧虽千差万别,笑却总是大同小异;然而,此论颇值得怀疑。关于出声的笑,语言表达异常丰富:咯咯地笑、嘎嘎地笑、哧哧地笑、轻声地笑、尖利地笑、暗暗地笑、愤怒地笑、放肆地笑、痉挛地笑、朗声而笑、粗声狂笑、纵情大笑、捂嘴偷笑、咆哮地笑、嗤嗤地笑、狂野地笑、放肆地笑、轻蔑地笑、傻傻地笑、哭闹地笑、刺耳地笑,凡此种种。笑起时,或狂暴而至、席卷而来,如狂飙,如罡风;或柔若涟漪,或急如湍流;或高声鸣响,声若号角,或细如涓流,旋转萦绕,或穿云破空,啸啸作响。论到微笑,也是品类繁多:粲然而笑、得意而笑;咧着嘴笑、觍着脸笑;讥笑、傻笑。微笑触动视觉,笑声触及听觉,不过,T.S.艾略特在《荒原》中曾用一行诗将二者融于一体:“浅笑在耳畔回荡。”
嘎嘎地笑、捂嘴偷笑等说法,意指笑的不同形式,涵盖诸如音量、声调、音高、速度、力量、节奏、音色、时长等性质。此外,笑也能传达一系列情感态度:欢乐、讥讽、狡诈、喧嚣、温煦、邪恶、嘲弄、鄙夷、焦虑、释然、冷嘲、会心、得意、淫邪、质疑、尴尬、癫狂、同情、轻佻、震惊、好斗、讽刺,更遑论不含丝毫愉悦、纯以“社交”为目的的笑。诚然,上述所列之笑的形式,多与幽默关系甚微,或是毫不相干。虽然兴奋时,目之所见会显得趣味盎然,但出声的笑更多源自情绪高昂,而不是忍俊不禁。笑的形式与情感态度可以衍生出多种组合,因此,窃笑可出于紧张,也可出于轻蔑;尖声大笑可出于善意,也可出于挑衅;咯咯笑或是出于惊诧,或是出于愉悦;嘎嘎笑或是出于赞赏,或是出于讥讽;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纪录片《笑》(1979)海报。
如此便生出一个悖论来:虽然笑本身纯粹是能指问题,仅有声音,没有意义,但社会生活却将其彻彻底底编了码。它是自然发生的身体行为(至少多数情况下如此),却带上了特定的社会意义,就此栖身于自然与文化之间。笑一如舞蹈,均为身体语言(笛卡尔称之为“含混不清的爆炸性呼号”),但身体亦深陷更为概念化的意义当中。即便如此,在那个曲高和寡的领域,它绝不会百分之百地安生自在,总会多出些粗粝的物质性,突出于意义之上。也正因如此,我们才得以尽情享受幽默。笑也鼓励我们坦然接受身体与意义间的失谐。特别是闹剧,往往能将身体与头脑间这宿命的冲突,生动地展现出来。
笑纯是发声,除其自身,不做任何表达,因而它不具备内在意义,一如动物的叫声。可尽管如此,它却充分承载了文化意绪。在这点上,它与音乐沾亲带故。笑不仅缺少内在意义,当其最为恣肆癫狂时,也会将意义解体,正如身体将话语撕成碎片,本我将自我抛入暂时的混乱。就像悲恸、剧痛、极度的恐惧或无端的愤怒,喧嚣之至的笑声意味着身体失去自控,那一刻它挣脱缰绳,使人退回身体缺乏协调性的婴儿状态。说到底,它就是一种身体失衡。笑包含着令人不安的动物性,其重要原因在于,笑声如呵呵声、嘶吼声、咯咯声、嘶鸣声、咆哮声,令人意识到我们与动物的类同性,这点颇具反讽意味:动物自己并不会笑,或者至少不会笑得这么明显。在此意义上,笑兼具动物性与显著的人性:模仿兽类的叫声,而自身又不具兽性。当然,笑是无处不在、司空见惯的人类乐趣。在《笑忘录》中,米兰·昆德拉援引法国女权主义者安妮·莱克勒克的观点:“无拘无束的笑声爆发出来,反复回旋,激荡冲突,这是肉体欢愉的笑声,是笑的肉体欢愉,去笑就是去恣意地生活。”

《笑忘录》,[法]米兰·昆德拉著,王东亮译,上海译文新文本|上海译文出版社,2019年2月。
如此看来,笑确有所指,但它也将指意分解成纯粹的声音、痉挛、节奏与呼吸。一个人笑得倒地抽搐、不能自已时,很难说出头脸齐整的句子来。在众多笑话中,连贯的意义断裂了,这体现在笑本身的解构性质上。这一暂时的意义混乱,最为明显地表现在各式荒谬、滑稽、无意义、超现实当中。然而,若说它是一切成功喜剧不可或缺的特质,似乎还值得商榷。一方面,笑体现了符号王国暂时的崩塌或分裂,而在这个王国中,意义本是有序而明晰的;另一方面,笑从未脱离对这个王国的依赖。除非只是给人挠了痒,或为了化解抑郁,抑或暗示同伴有他/她陪伴甚为快乐,我们的笑总会指向某些事物、事件、言谈、情境。因此,探讨笑这一现象需要使用概念,这也是为什么某些评论者声称,缺乏语言能力的动物不会笑。笑是一种言语,自身体的力比多深处腾跃而出。然而,它也有认知的维度。一如愤怒或嫉妒,笑也涉及信念与假设。
诚然,笑能够自内积蓄一股难以驾驭的力量,于是,刚笑没多久,我们便会忘记起初为何发笑,抑或觉得自己是为了笑而笑。这就是米兰·昆德拉再次援引安妮·莱克勒克时所说的“笑是如此好笑,它引人发笑”。还有一种笑具备感染力。我们发笑只是因为他人在笑,并不需要知道人家觉得什么如此好笑。你笑了一场,却并不能确定笑自何来,就像是某些疾病,不知是在哪儿惹上的。然而,总的来说,笑改变了头脑与身体的关系,却并未将这一关系彻底悬置。
有一个事实值得关注:以上所言大多也可用来讨论哭泣。詹姆斯·乔伊斯在《芬尼根守灵夜》中提到“笑泪”,而他的同胞塞缪尔·贝克特在《莫洛伊》中写到一个女人,她的小狗刚死掉,“我觉得她就要哭了,理该如此嘛,可相反地,她却笑了。也许这在她就是哭。或许是我搞错了,她真是在哭鼻子,只是听上去像笑。泪与笑,在我看来十足是盖尔人的风格。”实际上,笑与哭并不总是易于区分。查尔斯·达尔文在其情感研究中指出,笑容易被误解为悲恸,因为在这两种情况下,泪水都会汹涌而至。在《裸猿》一书中,人类学家戴斯蒙德·莫里斯论到,笑确乎自哭进化而来。

简言之,笑并非一开始就是在笑可笑之事。在非洲、西伯利亚等国家和地区,笑曾是致命的传染病,据称会歇斯底里地突然爆发,致使成千上万的人死于非命。1962年,在当时的坦噶尼喀省爆发了类似的案例,整个学区接连数月处于瘫痪状态。因为失控绝不会令人深感快慰,所以笑轻易便会惹人不悦。在其《词典》中,塞缪尔·约翰逊将笑定义为“突如其来、无法控制的快活”,但这种体验并不总是愉快的。这与被人搔痒有共通之处:快感与难耐奇妙地混合着。就像观看一部恐怖片,欣喜、不安、激动、不适的感觉会同时降临。猴子龇牙咧嘴,看似微笑,实则是发出警告。劳伦斯·斯特恩所著《项狄传》中的叙述者满嘴跑火车,居然告诉读者,有次他笑得太狠,一根血管爆了,两个钟头便流掉四品脱的血。小说家安东尼·特罗洛普阅读一本喜剧小说时笑得中了风,这番遭遇他自己的读者倒未必会有幸经历。尽管笑有着潜在的灾难性,它也能显示出人类的进步:只有当一种动物学会用手拿、而不是用嘴叼物体时,才可以腾出嘴来发出轻笑或窃笑。
笑与弗洛伊德
在《笑话及其与无意识的关系》中,弗洛伊德坚定地认为,笑话代表心理能量的释放,而人们通常用此能量维持某些基本的社会性压抑。为了舒缓对超我的压抑,我们减轻了该压抑所要求的无意识压迫,将节省的能量转而用于玩笑,以及出声的笑。可以说,这是笑的经济学。如此看来,笑话便是扇超我一记不恭的耳光。这般俄狄浦斯式的遭遇战令我们兴奋不已,可良知与理性也是我们尊崇的人性特征,由此便在责任感与放纵之间产生出张力来。

电影《大象骗人》(1976)剧照。
黑格尔在其《美学》中指出,无法遏制的感性冲动与高尚的责任感之间的冲突,造就了荒谬可笑之事。此冲突反映在喧闹的笑声中;此前已经说过,这等笑声可以令人警觉,也可以令人愉悦。我们笑得紧张,是因为这种越轨的欢乐令我们既提心吊胆,又乐在其中。正因如此,我们一边畏畏缩缩,一边掩口窃笑。然而,负罪感给快乐羼入某种别样的趣味。尽管如此,我们也清楚,这纯粹是临时的胜利,是纸上的胜利,毕竟笑话只是一段话而已。快活后的第二天,太阳照常升起,照见一千个空空的酒瓶、啃过的鸡腿、失却的贞操,日常生活回到正轨,人们感到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释然,或者,来看看舞台喜剧。观众从不怀疑,台上人物欢天喜地地撕碎的秩序,终将得以恢复,甚至就因为这一短暂的颠覆企图,会进一步得到加强。于是,在观众的内心,无政府主义的快感与一丝矜持的自诩混杂一处。就像本·琼生的《炼金术士》、奥斯丁的《曼斯菲尔德庄园》与苏斯博士的《帽子里的猫》,在父母角色缺席的时候,我们会无法无天、大闹天宫,可听说他或她也许一去不返,便会伤心欲绝。
弗洛伊德指出,在较为温和的笑话中,受压抑的冲动得以释放,幽默油然而生;在粗俗或侮辱性笑话中,幽默源自压抑本身的缓解。渎神的笑话也让我们身上的禁忌得以松解,比如教皇与克林顿死于同一天那个笑话。由于官僚主义错误,克林顿被送上天堂,而教皇被罚下地狱。不过,这个错误迅速得到纠正。二人上下交错之时,得以相交一语。教皇说迫不及待要见到圣母玛利亚,而克林顿跟他说,他晚了十分钟。
在弗洛伊德看来,笑话的那些有趣的形式(文字游戏、胡言乱语、荒唐联想,等等)或许一时间使超我放松警惕,令无政府主义的本我得到机会,将遭禁的情感推到明处。弗洛伊德将笑话的语言形式称作“前乐”,它放宽了禁忌,让人松弛下来,以此来劝诱我们,去接受笑话的性与攻击性内容;换作他法,或许很难说动我们。在此意义上,笑击败了压抑;然而,我们之所以感到趣味盎然,是因为冲破禁忌的举动,本身就等于承认了禁忌的力量。因此,如桑多·费伦齐所言,一个道德完美的个体不会比一个恶贯满盈的个体更爱笑。前者原就不会隐藏见不得人的情感,而后者不会承认禁忌的力量,所以在打破禁忌时,也不会倍感兴奋。正如弗洛伊德所言,我们觉得自己道德高尚,其实未必;我们认为自己道德低下,其实也未必。一如神经官能症的症状,宣泄论语境中的笑话也是妥协的产物,融合了压抑行为与受阻的本能。所以,弗洛伊德眼中的笑话,是个两面三刀的恶棍,同时侍奉两个主人。它对超我的权威卑躬屈膝,同时也不遗余力地促进本我的利益。

《诙谐及其与潜意识的关系》,[奥]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著/车文博主编,九州出版社,2014年6月。
大量幽默涉及弗洛伊德所谓的反崇高。当某种崇高的理想或高贵的第二自我被粗暴地戳穿,投入其中的能量便释放出来。维持此类理想需要一定程度的紧张感,因此,放弃维持便会令人如释重负。此时,受人尊敬的道德外表无须继续维持,人便可以毫无顾忌,变得粗鄙不堪、玩世不恭、自私自利、迟钝愚笨、侮慢无礼、道德冷漠、情感麻木、恣意放纵,并对此甘之如饴。不过,人们亦可以开心地从意义创造的急迫感中解脱出来。弗洛伊德称此急迫感为“逻辑强迫症”,即将不受欢迎的限制强加给自由不羁的无意识。因此就可以理解,为何在一个具有无限可能性的世界里,我们钟情于超现实与荒诞的事物。

电影《冒牌天神》剧照。
十九世纪哲学家亚历山大·贝恩曾谈到“生活中众多的清规戒律,迫使人们摆出别扭刻板的姿势”,作为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他尤其会注意到这些限制;幽默能让我们暂时摆脱的,也正是这种古板的世界观。
桑多·费伦齐本着同样的认识指出,保持不苟言笑成功地压制了自我。通常所谓意义,实为“高大上”的一种表现,造成轻度的压力,而开玩笑便是度一个释放压力的短假。社会现实的构建大费周章,需要不懈的努力,而幽默令人们的头脑得以放松。似乎在人们的理性官能之下,暗伏着一个黑暗、凌乱、玩世不恭的潜文本,与惯常的社会行为如影随形,间或以疯癫、违法、色情幻想或机智调侃的形式爆发出来。潜文本大多以哥特小说等文学形式侵入日常世界。这也让人想到蒙提·派森的一个小品:一个店家正赔着笑脸伺候一位顾客,却突然间爆出一连串污言秽语,可一转眼,又恢复了平时谦恭的自我。另一方面,有的幽默出自压抑,而非对压抑的反抗。比如那些健康、干净、友好的玩笑。男童子军的恶作剧与通常男性间的捉弄行为充满攻击性和焦虑感,为的是回避细腻情感与复杂心理,因为后者对他们那个抡起毛巾互抽、密林中赤身敲鼓的世界构成了威胁。
笑与两种人类存在观
在《笑忘录》中,捷克小说家米兰·昆德拉对比了两种人类存在观,即他所说的天使观与魔鬼观。天使观认为,世界是有序和谐的,意义填满了每一个缝隙。在天使的王国里,万物在形成的瞬间便具有了意义,不允许有一丝含混,令人感到压抑。整个现实清晰易读,却也枯燥乏味。对于重度偏执狂患者,根本不存在随机事件,没什么可以视情况而定。发生的就是必然的,是某个宏大叙事的一部分。在此叙事中,存在的每个特征,都有固定的功能。没有负面的、扭曲的、不健全的或功能失调的事物;这种乏味的天使观认为,人类正满面春风,高喊着“生命万岁”,大踏步向未来迈进。
与此观点相应的,是一种颇具教养的笑,是面对一个齐整有序、意义充沛、构思精妙的世界时,发出的愉快的笑声。米兰·昆德拉生命前几十年所亲历的世界,便是这类世界的一例。当代美国意识形态也颇为相似;在美式现实中,受到“你能够成为任何想成为的人”这一观念的影响,人们身不由己,拼命积极向上。这是一个令人鼓舞的世界,没有灾难,只有挑战。昆德拉认为,它所产生的言说“句句实情”,相反,魔鬼观的言说尽是废话。我们已经看到,一个世界若剔除了意义与价值,就只有魔鬼在尽情狂欢。这个世界里,万物皆粪便,难以相互区分。天使观的麻烦在于意义过剩,而魔鬼观深受无意义之苦。

电影《楚门的世界》剧照。
即便如此,魔鬼观亦不乏用途。好比珠母贝里的砂砾、装置中的差错、任何社会秩序中反常而执拗的因素,它对于社会存在的作用,在于打破天使观四平八稳的确定感。这样,它便或多或少与拉康式实在相类同。在魔鬼呵呵的嘲笑声中,自命不凡的天使丢了底气,没了先前的张扬。正如魔鬼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中所说的那样,魔鬼观带有一种任性而执拗的元素,防止世界因自身令人窒息的乏味而不堪重负,倒塌崩毁。魔鬼对伊凡·卡拉马佐夫说,在上帝创造的世界中,他起到摩擦或否定作用,谨防这世界由于无聊至极而萎缩。缺了他,世界将“一无所剩,除了对上帝的赞美”。若清除了这个异端因素,宇宙秩序便会崩塌,令一切终结。魔鬼天生就是解构主义者。
这种幽默,究其源头,在于事物暂时失却其在整体格局中的固有角色,导致失序、疏离与陌生化。我们笑,是因为某些现象似乎陡然失其常态,某些事情突然失去控制、乱作一团。这般滑稽的情形,使人得以暂时脱离清晰有序、不容置疑的世界,获得喘息之机。那是一个失去纯真的世界,它存在于先,人类灾难性地堕入意义在后。滑稽用例如笑话或机智的调侃,搅扰了宇宙的平衡;或者,用蠢笨、怪诞、荒谬、超现实的方式,将宇宙自身连贯的意义涤荡干净。本身毫无意义的笑声把意义的严重流失表现得淋漓尽致。因此,魔鬼观与幽默常常相连,便不值得大惊小怪了。同样正常的是,地狱中向来就回响着堕落的灵魂发出的下流笑声,窃笑、狂笑、幸灾乐祸的嘎嘎笑。他们自信已经看透了人的价值:揭开其真容,不过是言词虚华的欺诈。
托马斯·曼在《浮士德博士》中也谈及这类笑声,认为它带有“恶魔般的讥讽意味”,是“狂呼、嘶叫、咆哮、哭诉、嚎叫、尖叫”造就的“地狱式的快活”,是“地狱中含讥带讽、得意扬扬的笑声”。魔鬼与天使的对立,便是伊阿古与奥赛罗的对立,或者说,是弥尔顿笔下郁怒的撒旦与小官僚般饱受压抑的上帝之对立。波德莱尔曾写道:“笑具有撒旦性质,因而蕴含着深刻的人性。”凡夫俗妇极易轻信,他们热切地认为,那无谓与单薄的意义与价值像铁熨斗一般坚实,真是可悲可叹。目睹这些,魔鬼们爆发出难以置信的大笑,压都压制不住。

《浮士德博士》,[德]托马斯·曼著,罗炜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年4月。
阿莲卡·祖潘季奇的喜剧研究颇具新意。她认为“此世界的构成自相矛盾、因势而变”,笑话即是其缩影。人的意义建构具有偶然性,缺乏依据。笑话的功用在于将这点提升到意识层面。可以说,笑话是藏匿于语言象征秩序内的真实,而该秩序看似自然,实则是现实的理性版本。构成该秩序的能指,实际是随意的符号与声音;若想有效运作,它们必须足够灵活、含混,能够自由浮动,从而以各种不同的方式结合,包括荒唐与反常的方式。因此,从逻辑上讲,构成意义的也能构成无意义。二者相互依存,缺一不可。祖潘季奇认为:“普遍的无意义是一切意义的先决条件。”
弗洛伊德也持此观点:无意义是意义的根基。雅克·拉康写道:“笑话的价值在于,它能够利用一切意义实质上的虚无性。”社会现实的建构随形而变,笑话透了这个底,由此也揭露了现实的脆弱性。祖潘季奇评价道:“在一定程度上,每个笑话都道出了,或者说展示出我们这个世界本质上的不确定性与危险性。”此论也适用于亲属角色的有序结构;它是一个象征秩序,由一套确定恰当组合的规则所统御。在本质上,这类秩序若能正常运作,则必能非正常运作。规范该秩序的诸种规则,能够对众角色进行合法的排列组合,也能够产生出非法的排列组合。乱伦即是一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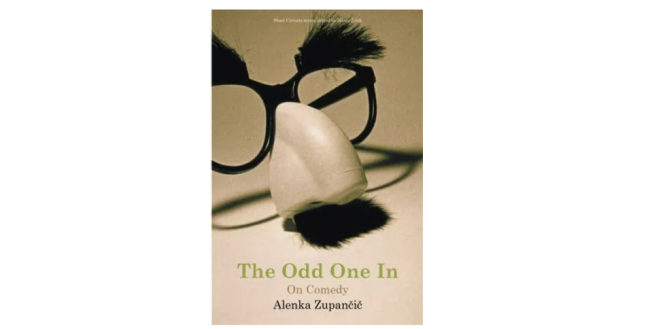
阿莲卡·祖潘季奇所著的《怪人来了:论喜剧》(The Odd One In: On Comedy)英文版书封。
社会意义的不稳定性,在局外人眼中或许最为明显。所以,从威廉·康格里夫、法夸尔、斯梯尔、麦克林、哥尔德斯密斯,到谢立丹、王尔德、萧伯纳、贝汉,主导英国戏剧舞台的,是一个个移居来的爱尔兰人。这些作家漂到伦敦,身无长物,唯有兜售其机智与诙谐,进而将其局内人/局外人的混合身份,变为成果斐然的戏剧实践。他们都操英语,其中几位还是英爱混血,对英国本土的社会习俗相当了解,能够做到了然于胸;同时,与那些习俗也保持着足够的距离,令他们能以讥诮的目光,敏锐地发现其荒谬之处。英国人眼中似乎不证自明的假设,会令他们感到假得出奇;喜剧艺术就是从这反差中采撷而来的。自然与矫饰的冲突,是喜剧的恒久主题。最能敏锐地感受到这一点的,是这些爱尔兰作家。虽然经常流连于英国的俱乐部与咖啡馆,他们却真切地感到,在伦敦文人圈内,自己不过是访客而已。

电影《喜剧之王》(1982)剧照。
可见,喜剧存在的目的,就是颠覆宇宙。此处的宇宙,指的是一个理性的、道德的、美丽的、有序的整体。若此言非虚,则某种意义上,它便是个反讽,因为“神曲(神圣的喜剧)”这一表述意指的就是这个观点。在其形而上学意义上,喜剧反映出准神秘主义信念:虽然看似相违,一切在根本处都与人性相合。《新约》在此意义上便是部喜剧文献,虽然它很清楚,为此信念付出的代价高得骇人,不是死亡,就是自我放逐。舞台喜剧在形式层面保留了秩序与设计感,却用颠覆性的内容质疑这种均衡。似乎形式是乌托邦的,或者合乎天使观,而内容是讽刺性的,合乎魔鬼观。最终,一部喜剧往往从后一状态向前一状态迁移。这个行动或许围绕着象征秩序的某个危机展开。然而,其最终目的是修补、恢复与和解。由此,围绕危机的喜剧让位于围绕宇宙秩序的喜剧。经历一番搏斗之后,天使观战胜了魔鬼观。
原文/[英]特里·伊格尔顿
摘编/青青子
导语部分校对/张彦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