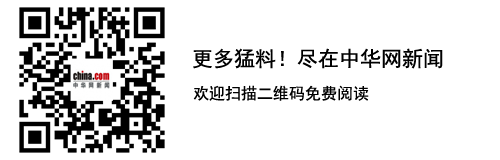孔丹回应秦孔之争:爆粗口都是网上造谣
原标题:孔丹回应“秦孔之争”:爆粗口都是网上造谣我们还是发小
“半生长卷已斑斓,更有殊才上笔端,最是较真终不改,难得本色任天然。”2012年,孔丹过65岁生日时,时任国务委员马凯送给了他这首诗。
“我是很本色的人。”中信集团原董事长、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理事长孔丹坦然道,“我也想过率性的生活,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而回首我这一生,很多时候都在被动地做选择。”
孔丹出身于一个“红色家庭”,父亲孔原为原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母亲许明为原国务院副秘书长。他曾因“西纠”两度遭到囚禁,父母也因此被名为“西纠黑后台”,父亲被关押多年、母亲自杀。这段经历是他一生的梦魇。
1978年孔丹考上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的硕士研究生,成为其开门弟子。硕士毕业后,历任国家经委主任张劲夫的秘书、光大集团总经理和中信集团董事长。在掌管两大央企期间,成功主持应对了光大信托巨额亏空事件,中信银行三百亿不良资产处置以及改制上市和中信泰富炒汇巨亏事件的三次重大危机。在他的带领下,中信集团成功渡过2008年金融危机,并于2009年首次进入“世界500强”。
1984年是孔丹的转折点,他称这次转折是他唯一的一次主动选择。此前一年,王光英组建了光大,他亲笔给张劲夫写信力邀孔丹加入光大。时任中信业务部副总经理、孔丹的老大哥王军也极力说服孔丹去中信。而张劲夫则希望孔丹继续从政。最终,孔丹选择了光大并将秦晓推荐给了王军。“我这一生一直处于被动的选择,别人可能有很强的主动权。去光大、中信还是从政,这是我回想第一次自己做的选择。其他的选择,我基本跟着实际的变化而变动。所以,我不后悔。”孔丹说道。
他被誉为光大四朝元老,谈及光大的16年,他表示自己有遗憾,“光大的发展不如人意,波折比较多,领导更换太多,不像中信一路发展下来有比较平稳的领导班子沿袭和过渡。”
2000年,孔丹离开光大正式加入中信集团,与自己的老大哥原中信集团董事长王军搭档了6年。期间,他们共同推动中信集团的更名改制,奠定了中信集团金融业的发展方向。2006年,掌舵中信集团近11年之久的董事长王军卸任后,孔丹接棒。谈起在中信的10年,孔丹说:“在我任董事长期间做了很多努力,比如中信银行上市、处理中信泰富危机。我那时特别努力想做的事,即中信集团整体上市,最终也实现了。所以,也没有什么遗憾。”
“我不得不承认,实践把我塑造成了一个国企干部。我不像很多企业家会说自己成功,我自己这一辈子都在转危为机,败中求胜。我很多事都被推着走,光大信托不是我拉的屎,我得去擦屁股;中信银行不良贷款是长时间发展积累下来的风险问题,它也不是我直接造成的;泰富危机并不是我惹的祸,但我们最终还是救了它。很多事情不是你想不想做,而是被逼着去应对。”孔丹说道。
2010年12月27日被正式宣布卸任中信集团董事长。“我很庆幸,在我退休的时候,是时任国家副主席习近平亲自找我谈话,对我工作表示认可和肯定。近平同志说:‘你在中国改革开放的两个窗口——中信,光大多年,工作卓有成效’。虽未盖棺但已有定论,我觉得就该可以了”。
原本功成身退的他以为可以归于平淡,但2013年的“秦孔之争”再次将他卷入舆论漩涡。“我很无奈,这个转折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但网上传言我们吵架、骂脏话,这绝对是造谣。我和秦晓只是在一些问题上意见相左,我们毕竟还是发小。我既不是“左派”,也不是“右派”,我是实事求是派。”
在完成口述史《难得本色任天然》后不久,孔丹开始筹备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2014年8月,基金会正式成立,孔丹担任理事长,并为中信基金会制定了三条宗旨:坚持实事求是,践行中国道路,发展中国学派。孔丹提出,“以前跟商界朋友叫呼朋唤友,现在跟理论界叫称兄道弟。现在已经快5年了,这是一个虽然艰苦但很有意义的事情。我也从经济战线转到了理论战线。”
“我很少说,为什么我不想从政?因为枪打出头鸟。在文革初期我也有错误,但是后来已经纠正了,而且那并不是我的初心。我很多事情都被推着走,没有选择。”孔丹说道。

孔丹:说我参与了莫干山会议不太准确,我是会议的传声筒
凤凰网财经:1982年至1984年,您到国务委员兼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办公室工作,担任时任国家经委主任张劲夫秘书。当时,您的导师吴敬琏先生希望您出国深造,后来为何选择了从政?
孔丹:1981年,我研究生毕业,分配到经济研究所当助理研究员。当时正好有一个机会,福特基金会资助一批中国学者到美国做一年期访问学者,结果这时任命我当秘书的调令来了。时值张劲夫同志从安徽调任到北京,担任国务委员兼国家经委主任。当时,我非常犹豫,原本我已认定要在经济学理论领域走下去。劲夫同志就找我谈了一次话,说“这个机会很好。搞理论工作也要解决实际问题,我这里可以接触各方面的人,也有很多你熟悉的年轻人,你们可以多沟通。我们也需要你这样的人才。”这样,我就离开了理论战线转而从政了。
凤凰网财经:您在2017年出任莫干山研究院名誉院长。早在您任张劲夫秘书期间,就参与了著名的“莫干山会议”。这次会议形成了莫干山会议成果,坚定了中央物价改革的信心。当时的情景是怎样的,哪些学者给您的印象深刻?
孔丹:在1980年代,我跟一群同时代的年轻人保持了比较密切的交往。他们在莫干山研究一些关于改革开放实践方面的问题,我听了非常感兴趣,当时就给劲夫同志提出想要听会的想法。后来,我就去了。我记得当时有农村政策研究院的翁永曦、王岐山、朱嘉明和黄江南,号称“四君子”,还有徐景安、周其仁等。
我记得到了莫干山那天,大家讨论激烈,彻夜未眠。王岐山和纯粹理论学术派风格不大一样,他一贯表现出很强的为政府咨询、为决策服务的能力。我当时就把各种意见搜集起来,整理了一个报告,交给了劲夫同志。劲夫同志看了材料后,召开了一次座谈会,再次听取了大家的意见。
我参与了莫干山会议不太准确,我给自己的定位是他们的铺路石和传声筒。但这个作用在当时没有人能替代,我提供了一个渠道,将大家的意见上达到国家经济改革开放的决策中去。特别关于物价改革的讨论,当时莫干山会议讨论了渐进式、双轨制式甚至彻底市场化的改革,这对之后物价改革形成了助力。当时劲夫同志也是国务院物价改革领导小组的组长,决策层也一直在研究物价改革的问题。为此,劲夫同志还多次跟陈云同志汇报,听取他的意见。最终,物价改革采取了渐进式的方式。
孔丹谈“光大16年”:有遗憾但不后悔
凤凰网财经:1983年,您加入光大集团,负责沿海城市业务部。为何想到去企业发展?当时,时任中信业务部副总经理王军先生也极力邀请您加入中信。为何最终选择了光大?
孔丹:1984年,我正要离开时任国务院国务委员兼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张劲夫同志时,有一个特别的经历。此前一年,王光英同志组建了光大,他亲笔给张劲夫同志写信邀请我加入光大。当时王光英的助手李新时、刘基辅还找到我专门说到那封信,我说劲夫叔叔没有提过这件事情。后来,我去家里找劲夫叔叔,他半天不说话,之后拉开了办公桌的抽屉,然后拿出一封信说,确实有这样一封信,但我不希望你走。他希望我从政,去做党政干部。
当时,王军也找到我,希望我加入中信。因为我的事情,他还给中信创始人荣毅仁讨价还价,说“孔丹去光大职务较高,如果加入中信至少也应该是部门副总经理职位。”那时他自己也就是业务部副总,足见他对我的看重和厚爱。
最终我还是选择去了光大,王军因为这个事情记了我一辈子,随时敲打我,说我嫌他给的官小所以没有选择中信。我当时给他解释,“我愿意追随你,但中信人才济济,光大更缺人。”这么诚心实意的老大哥,我们这么多年的交情,我也不能对不起他,我就给他推荐了秦晓。我说秦晓各方面都比我强,而且英语比我好,比较适合外贸工作。他痛骂了我一顿,最终,还是接受了。
凤凰网财经:1990年,光大差点被取消了,后来怎么保留下来了?
孔丹:当时社会舆论汹汹,公众认为工商联公司、光大、中农信、康华和中信五大信托公司谋取私利。当时在北戴河开会,第一次决定保留中信,撤销其它四大信托公司。
当时,我和光大一些老同志写了联名信。我们提出,“光大已在香港经营多年,建立了多方联系,如果撤销可能会有负面影响。”当时光英同志已担任副委员长,作为创立人,他肯定为此做了大量的工作。最终,光大被成功保留了下来。
凤凰网财经:那时,您有后悔当初的选择吗?
孔丹:我没有什么后悔。我觉得,我这一生可能都处于很被动的状态,可以说当时选择去中信、光大,还是从政,这可能是我回想起来,人生唯一的一次自己主动的选择。
凤凰网财经:您对光大这16年有什么遗憾吗?
孔丹:外界把我叫做“光大四朝元老”之一,之前有王光英董事长、邱晴董事长、朱小华董事长以及刘明康董事长。我对光大是有遗憾的,光大的发展不如人意,波折比较多,领导班子换得较多,不像中信的领导班子比较平稳地沿袭和过渡。
我处理过光大危机,光大信托投资公司是中国金融业发展的一个写照,在发展初期,由于需要资金,采用了高息揽存,扩张投资,导致资产质量不匹配,偿付能力不匹配,最终形成了重大的危机。
当时光大信托负责人是王亚克,他在短时间把光大信托投资规模从9个亿扩张到140亿,这些钱有的投入到了项目,有的放贷了,实际上是血本无归了。而这些资金实际上是通过高息揽存形成的债务,人民币年息22%至24%,美元年息12%,每年成本在25亿以上,偿付能力不匹配。同时,王亚克在做外汇交易时也出了问题,亏了8000万美金。这次危机惊动了中央,调整了光大的领导班子,邱晴因此被免职。90年代初,新任光大董事长朱小华带着我们一起去了北戴河做汇报。国务院召开办公会议,专门研究光大问题。李鹏总理、朱镕基副总理、李岚清副总理和钱其琛副总理等出席了这次会议。会议由李鹏总理主持,镕基副总理在一边不断插话。当时几个副总理都非常着急,李岚清副总理说:“你们这里有外贸系统的钱,不得不还。”钱其琛副总理说:“我们外交系统本来就没几个钱,放在你那儿生点利息。结果搞成这样,你们得还。”
那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我常用的词就是:坐困愁城、内无粮草、外无救兵、难以为继。最终确定的方案,除了少数还钱以外,基本都债转股。后来,方案中债转股部分遭到强烈抵制,我们又就做了妥协,延期还款。
孔丹谈“中信更名改制”:一开始朱镕基总理没有同意
凤凰网财经:2000年7月,您从光大调任中信集团副董事长兼总经理。当时调任的背景是什么?
孔丹:当时,中央组织部部长找我谈话:“你调动一下,中信规模比光大规模要大。我们在五十多个机构做了调研,考虑你更适合这个职位。你和王军也比较熟悉,能更好地配合他的工作。这是中央的决定。”
不久之后,秦晓调到了招商局任董事长,执掌一方。秦晓的调动很正常,他在中信待了十几年,新岗位的空间更大。后来,我还曾和秦晓开玩笑,“从领导班子配对来看,你配合王军董事长5年,我配合了6年,比你还多1年。”
凤凰网财经:当时遇到过什么比较大的困难吗?让您印象深刻的事情?
孔丹:当时,我们遇到一个情况,中信要不要发展综合金融。中信集团原来叫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属于非银行金融机构。我们要改名为中国中信集团公司,希望把原来的金融性机构转为集团下属业务,包括中信银行、中信证券、中信信托、中信保诚保险公司等。2003年,我们专门跟国务院做了报告,当时我陪着王军去给马凯副秘书长陈述,提出希望把中信变成一个金融控股公司概念来运营。
最终,镕基总理没有接受这个意见,他同意中信集团重组,但在中信集团成为金融机构问题上并没有松口。为什么?因为当时中国监管经营模式是分业经营分业监管。如果成立一个金融控股公司,这与法规不合,现有的监管模式也不能匹配。中信集团本身不能做金融机构,不能从事金融业务,后来,我们就变成了控股公司的模式,这个模式一直持续到2014年在香港上市,基本维持这样的基本框架。
2003年的这个重大改革也得益于早期王军和秦晓所推动的战略布局。早期,王军和秦晓就开始缩短战线,把业务调整更集中,为后来金融和非金融业关系处理作了铺垫。在这次改制后,中信集团基本处理好了金融和非金融业的关系,形成金融和非金融相对均衡发展的局面。
很多金融集团公司可能曾想成为金融控股集团公司,最后,正路不走走了斜路,比如安邦系。
我认为混业经营模式还需要探索,应审时度势,既要看到金融控股集团模式的优势,也要看到它的风险。此前的几次金融性风险都和混业经营有关系,通过不同性质金融业务套利,脱离实业进行金融自我循环,资金出现层层套利。所以,这也成为了资管新规监管的重点。
孔丹谈中信证券上市:一开始就预测股价撑不住
凤凰网财经:2003年,中信证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成功上市,成为国内第一家公开上市的证券公司。当时,上市过程中遇到了哪些困难?
孔丹:当时证券公司面临共同的发展瓶颈,即怎么扩大物理网点,扩大客户群,以及拓展技术支撑。这都需要一定的资金。我觉得中信证券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资本市场的领头羊,一个很重要的基点是率先成功上市。
我记得时任证监会主席是周小川。我直接跟他进行了沟通,希望中信证券能成为首例上市证券公司。后来,我记得在上海敲钟的时候,我们一开始就预测股价挺不住。我记得时值冬天,我跟时任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王东明一起去敲钟。敲完以后,我就拉着大家去喝啤酒,不要管股价,要是盯着看,会伤心的,因为股价肯定撑不住。
凤凰网财经:为什么一开始就预测可能撑不住?
孔丹:因为当时,公众对中信证券这种形态比较陌生。我说中信证券和银行不一样,银行像蛙泳和自由泳,股价表现比较持续连贯,一个动作接一个动作,因为银行业务一直在增长。中信证券像蝶泳,高一阵子、低一阵子。
后来我们引入中国人寿时,他们投了140亿元,因为当时中信证券业绩不好,价格非常低。我跟他们说,你们不要看我们眼前的趋势,不要只看这张纸,要看这个纸上的箭头指的方向,纸以外的空间。
其后中信证券有了长足的发展,虽然经过2015年的波折,目前,依然是中国证券业或者中国投资银行业务的老大。我想王军董事长,无论生前还是身后,他都会很欣慰。
凤凰网财经:2006年,正值中信银行改制上市的关键时期,王军先生卸任了中信集团董事长,交棒给您。当时,您的压力大吗?
孔丹:王军喜欢说,困难没有办法多,我也信奉这个道理,任何困难,你只要努力,天无绝人之路。
孔丹谈“中信银行上市”:我拿着81亿“成绩单”跟马凯交了卷
凤凰网财经:当时中信银行改制上市面临着哪些困难?
孔丹:中信银行改制上市是中信发展的关键节点,信托业整顿刚结束,银行业整顿开始了。当时,镕基总理为工农中建四家银行剥离了14000亿不良资产,专门成立了四大资产管理公司。
中信银行和其它大型银行一样,由于风控管理薄弱、盲目扩张积累了大量问题。为顺应地方发展,曾承担了大量地方经济发展的融资功能,而很多地方不具备偿付能力,最终形成了大量坏账。
我记得,我跑到分行调研时鼓励分行负责人说实话,“不要怕业绩不好看,谁今天隐瞒不良资产越多,以后就会吃亏。我们要拨备核销,之后就不给指标了。”最后算下来,中信银行有超300亿的不良资产,当时的净资产只有50-60亿。如果报备核销200亿左右,我们就是一个负资产公司。当时国外有一种说法,中国整个银行业处于破产状态。
我配合王军推动中信银行消化不良资产和上市。2003年至2005年这三年,我们逐年注入资本金,但我们不能借钱只能向政府求助。
我配合王军同志找到了时任国家发改委主任马凯,请求政府批准中信集团发债。马凯同志说:“我们发改委是做项目的,只为项目批准发债券。”我说:“你可以把‘给中信银行补充资本金’当成一个项目。你放心,虽然目前资产状态不太好,但中信银行每年盈利五六十亿,所以,发债没有风险。”我在他家当面给他算了很多账,有一次算到三更半夜。
2003年,该方案由发改委报国务院批准。那年,我们发了100亿的债,2005年又发了90亿。这些资金拨到中信银行补充了资本金,核销了200多亿不良资产。
凤凰网财经:2007年,中信银行在香港和上海A+H股同时上市。当时顺利吗?
孔丹:2006年3月,我们启动中信银行上市工作。2007年,我们分别带队去欧洲、美国等地巡演。一开始,我们给证监会争取了40倍市盈率,最终,我们的认购倍数达到90倍,创造了当时中国银行业上市的最高纪录。最终,融资总额基本达到60亿美元,这对当时中型商业银行来说是一个非常令人鼓舞的业绩。当时有同事还打赌,如果认购倍数超过招商银行,每人给他五美元。最后,这个同事赚得盆满钵满。
中信银行上市,当时给投资人预测利润是每年57亿元,2007上市那年就达到了81亿。我就拿着“81亿”跟马凯交卷。我说:“超过当年跟你说的预测,干干净净的真实利润。”
凤凰网财经:当时上市成功,您和王军先生庆祝了吗?
孔丹:我们没有单独庆祝,王军有军人风度,他不喜欢喝酒,我可能在农村插队养成了习惯喜欢喝酒,比较江湖气。
不过,对于中信银行的上市,我们都非常高兴。如果没有这个转折,我们可能经受不住2008年的金融危机。由于中信银行的助力,中信集团整个盈利也有很大提高,从2001年的60亿元到2007年的160亿盈利,2008年,我们经受了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2009年,我们净利润为203亿,2010年已经到320亿,银行的贡献是极其重要的。
孔丹谈泰富危机:常振明当时夜不能寐我还睡得着
凤凰网财经:中信集团即将迎来30周年庆时,正值2008年金融危机那一年爆发了中信泰富(中信集团在港上市的联营机构)澳元期货合约危机。当时为何决定出手救市?现在来看,这个方案有哪些经验值得借鉴?
孔丹:当时,很多人在背后议论,中信可能成为“雷曼第二”。我当时感慨,不知明年今日是何处。常振明夜不能寐,我还睡得着,因为我进过监狱没什么怕的了。王军大哥还来到我的办公室。他说,“这恐怕是中信迄今遇到的最大危机,颠覆性的危机。”我说:“如果把我的乌纱帽摘了,我也无话可说。”
危机爆发后,我们从早到晚开会,在小黑板上列出救与不救各自的优劣问题。如果救,用什么方式?是否可以壮士断臂?如果不救会进一步造成交叉违约,而此前爆发全国信托危机时,全国都在赖账,唯有中信坚持兑付。这是中信的生命线,不能丢。
最终,中信集团决定出手施救,决定中信集团融资15亿美元,以每股8港元入股中信泰富,持股比例从29%增到57%,变成它的绝对控股股东;同时,把87亿美元的澳元期货交易中的2/3接到中信集团里。每澳元在0.7美元以上的损失,由中信泰富自己承担,跌到0.7美元以下的损失,中信集团承担。2008年12月19日,上述方案两个方案均获得股东大会99%票数通过。
我们亏了吗?我们算了一笔账,虽然我们以每股8港元入股中信泰富,当时市价4港元,相当于高于市价一倍买了股票,但净资产每股为16港元,相当于赚了8港元。后来每股涨到了15-16港元,中信泰富当年恢复了正常运行,次年净利润达到了59.5亿港元。
后来,中国推出了4万亿刺激计划。澳大利亚的铁矿石和焦炭又开始供应了,澳元也升值了,从7毛升到7毛以上,最终,算下来我们还赚了6-7亿美元。当时,我和常振明进门第一件事不是看股价,而是先看美元和澳元的汇率。当时,我记得去王岐山同志那儿作汇报时在门口碰到马凯同志。他还对我说,“澳元涨到7角1分喔。”我说,“你还替我操心呢。”
原本,中信银行上市后不久,我和常振明就提出了中信集团整体上市的计划,但后来被泰富危机打乱了。这次注资泰富使得中信集团持股从30%左右上升到65%左右,这一举奠定了2014年中信集团借壳“泰富”整体上市的基础。
凤凰网财经:2010年12月,您从董事长职位卸任。中信这10年有什么感触?有遗憾吗?
孔丹:光大领导层更换太多,中信相对于比较稳健。在我任董事长期间做了很多努力,比如推动中信银行上市和处理中信泰富危机。所以,我没有什么遗憾了。
2009年,中信集团第一次进入世界五百强,排名第415位。去年在常振明董事长的带领下达到了149位。我那时特别想做的事儿是实现中信集团整体上市,后来它实现了,也是香港的蓝筹股,所以,没有什么遗憾。
我很欣慰,我在企业干了几十年,2010年,在我退休的时候,时任国家副主席习近平找我谈话,对我工作充分肯定。习近平同志说:“你在中国改革开放的两个窗口——中信、光大多年,工作卓有成效。”这句话让我非常感动和欣慰。2011年,中央对我进行了经济责任审计,这次审计一共有13个特派员办,审计工作人员达数百人之多。最终,中央肯定了我这40年的工作。这一次审计相当于对我个人虽未“盖棺”先“定论”。我算是荣退了,我很高兴。
孔丹谈“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这是件艰苦而有意义的事
凤凰网财经:2014年8月,在您的倡导下,中信集团成立了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您亲自担任理事长,为何成立这个基金会?您目前的主要工作内容是什么?对于未来中国学派的发展,有什么建议?
孔丹:十八大以后,国家面临着重大的选择——反腐。当时,社会思想比较混乱,舆论斗争比较尖锐,我认为这时国有企业除了经济责任和社会责任外,应该承担起参与舆论斗争的政治责任。所以,有了成立中信改革发展基金会的想法。2013年,我们开始酝酿和筹备基金会。2014年,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正式成立。
我又从经济战线转到了理论战线。以前和商界朋友叫“呼朋唤友”,现在跟理论界叫“称兄道弟”。我为中信基金会制定了三条宗旨:坚持实事求是,践行中国道路,发展中国学派。坚持实事求是是成功的关键,同时,践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一定要坚决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学派强调理论建设和学术要求,我们不仅要发展哲学上的中国学派,政治学上的中国学派,在经济建设上也要发展中国学派。现在,基金会成立快5年了,这是一个虽然艰苦但有意义的事情。
孔丹谈“为何不愿意从政”:枪打出头鸟
凤凰网财经:回顾这些年的经历,您个人有什么遗憾?
孔丹:我个人喜好过率性的生活,希望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但是很多转折根本就意料不到。我不得不承认,实践把我塑造成了一个国企干部。我不像很多企业家会说自己成功,我大概一辈子都是“败中求胜,转危为机”。
我很多事都被推着走。光大信托不是我拉的屎,我得去擦屁股;中信银行不良贷款是长时间发展积累下来的风险问题,它也不是我直接造成的;泰富危机并不是我惹的祸,但我们最终还是救了它。很多事情不是你想不想做,而是被逼着去应对。
你还年轻,当你到一定年龄后可以设想下,哪些事是你特别想做的、主动想做的,一辈子很难。我可能就一件事是我主动想去做的,没有去搞理论,先做了官员从政了,后来,我不愿意从政了去企业了,这是我真正的选择。
很多朋友认为我是一个从政的料,为什么我不想从政?因为枪打出头鸟了。我曾经为别人去申诉,不应该把“三种人”的帽子扣在一批人士身上,但最终我再次成了出头的椽子了。在文革初期我虽然有错误,后来也都纠正了,而且这都不是我们的初心。
孔丹回应“秦孔之争”:骂粗口这都是造谣我和秦晓还是发小
凤凰网财经:您觉得外界对您有什么误解?比如2012年爆发的“秦孔之争”。
孔丹:这个事情我完全没有意料到,我也把我的很多想法给领导进行了沟通。大家可能对一些重大问题的认识有一定分歧。我也借此说,网上盛传的关于我们吵架或说我骂脏话,这绝对是造谣,是污蔑。我有一段时间很愤怒,后来,我明白了,网上有一个特点,越去辩解,人家越会抹黑你,我就不怎么在意了。
我和秦晓是有不同的意见和看法,有些意见分歧比较大,但这并不影响我们的关系,我们还是发小,现在我们也有一些联系。我既不是“左派”也不是“右派”,我是实事求是派。
我自认为我是实事求是派,并努力做到每件事情都实事求是。包括我对于一些重大问题的看法,比如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道路上,我认为我们不仅要把权力关进笼子,还要把资本关进笼子。资本是资本家的灵魂,资本的本性是增值,为了增值逐利会做出不利于社会的事情。每一个腐败案例的背后都有权力和资本参与其中,无一例外。
我也主张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共同发展。现在谈民营企业会提到“五六七八九”,即民营经济在整个经济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GDP,70%以上的技术创新,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的新增就业和企业数量。其实还有“五四三二一”是国有企业贡献的。五六七八九和五四三二一是相辅相成的,而不是国进民退或国退民进,这是一个伪命题。
我主张政府和市场两只手要共同发挥作用。我主张在科技发展过程中要吸取计划经济时期的举国体制1.0版的经验和教训以及改革开放以来举国体制2.0版的经验和教训。我们现在要探索建立举国体制3.0版,即中央提出的新型举国体制。
有人说孔丹是保守派,这帽子就给我戴上了。我有时想驳斥,文革结束之后,在国家改革开放的每个重要窗口期,我都参与了。我只能说,你要说我是什么派,我就是什么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