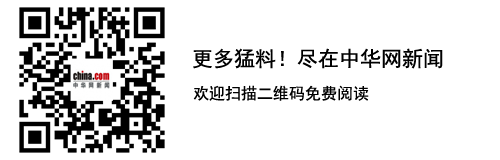肿瘤医院旁的小小假发店:她们在这里“戴”上生命的尊严
上海东安路从斜土路到零陵路的480米路段,是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门前的一条街。工作日白天,这里挤满来自全国各地的病人和家属,他们中大多数人有一个共同的敌人:癌症。
东安路沿街密布着各种针对病人的商业点,如药房、快餐店、小旅馆等,还有一家小小的假发店。这家假发店开在肿瘤医院正对面,癌症病人是主要客源。通常癌症病人在做化疗后第15天开始掉头发,于是不少人在化疗初期便把头发剃光,戴上假发。
头发还能再长,活着比较重要
从沿街的一扇门进去,穿过一家中药铺走到尽头,这家名叫“品秦假发”的假发店就开在这里。十几平方米的小店里有4个梳妆位,白色的货架上放满头模和假发。
假发店老板姓秦,原来是一名普通发型师,后来改行做假发。“刚开始就是为了做生意,把店设在肿瘤医院对面能带来更多客源。”老秦性情直爽,喜欢跟人聊天,客人来到店里,他都会先跟客人聊上两句,根据客人的治疗情况为他们选头发。但聊天时,老秦很小心,不过多触及敏感话题。
老秦说自己的店比较“专业”,店里的假发是专门针对癌症病人做的。为方便外地病人,店里除了卖假发,还提供一系列免费的“售后服务”:洗发、剪发、寄存行李箱、代收包裹、代收医院检查报告、寄存冷藏药品等。
“来这里的病人一般都很绝望,年纪越大越接受不了现实,情绪崩溃的往往是四五十岁的人。”老秦说,病人来配假发,进来和出去是不同的状态,进来时很郁闷,出去时心情会好一点。
店里出售的假发价格从几百元到几千元不等。全假发最便宜,混发(半假半真)稍贵一些,全真发最贵,一般都要上千元。客人大部分是女性,有的一开始准备买几百元的,挑着挑着就买了几千元的。为什么买贵的?因为头发关乎一个人的形象和容貌,是她们活着的尊严。
记者采访那天,店里来了个“短发”女孩。“来啦!”老秦熟络地跟她打招呼。“嗯,来洗头发!”她手捧一束花,往靠门口的位子上一坐,利落地摘下头上的假发交给店员,自顾自摆弄起手中的花。过了一会儿,头发洗好了,老秦把湿头发挂在一个头模上吹造型。他先用夹子把头发一层一层夹起来,用梳子翻蓬松,边吹边拉直。老秦说,在头模上做头发和在真人头上完全不一样,要想象它戴在真人头上的样子。
从谈话中得知,女孩家在昆山,每次化疗都是一个人当日往返,昨晚医院的机器坏了,她就在附近小旅馆住了一晚。店里的人对这女孩很熟悉,因为她是病人中少有的“元气少女”。“我以前是长卷发,长发及腰呢。”女孩说话声音明亮,笑起来还有浅浅的酒窝。“那时我刚被确诊,还没开始化疗,医生说一开始化疗就要掉头发,我就立马去发廊剪了个短发。开始化疗后,没过几天,短发也一点点掉了,我就直接剃了光头。”她摸了摸自己的脑袋,好像在说别人的故事。
当天晚上是她最后一次化疗,她特别高兴。“化疗结束后,我的头发就会长回来啦!头发没了还能再长,可是活着比较重要,你说对吧?”她的笑容就像春日里的一抹阳光。
父亲为女儿借顶假发拍毕业照
目前在中国,癌症患者的存活率很低,五年生存率仅30.9%。因此来店里做假发的客人,如果过一年半载见不到,很可能已经不在了。
去年7月的第一天,天气异常炎热。这天,店里来了一位父亲,想给女儿借一顶假发。“我们这里是卖的,不租借。”老秦告诉他。“是这样的,我女儿今年初中毕业,过两天学校要拍毕业照,她想和同学们一起合影。”父亲红着脸解释,“我们家条件不好,就想临时借一下,拍完就送回来。”听了这位父亲的请求,老秦答应了。
连说了三句“谢谢”,这位父亲跑出去把女儿喊进来。这是个16岁的小姑娘,瘦弱得好像一阵风就能吹跑,眼睛里没有神,化疗把她本来就弱的身子消耗得快虚脱了。在镜子前,老秦给她戴上假发。看着一头乌黑浓密的头发又回来了,她苍白的脸上终于有了点笑容。“好看。”她回过头对父亲说。
“我女儿以前就是这样一头长长的直发。”父亲打开手机里的相册,里面有女孩的许多旧照片。那都是一年多前的照片了,那时小姑娘活泼、健康,笑容灿烂。自从生病以来,她几乎没有拍过照。
那天,她借走了假发,三天后又如约还了回来。再后来,老秦给她做了顶专属于她的假发。“这姑娘一直断断续续做化疗,人也一天天不成样子。”老秦说,病人在化疗期间理论上每隔一段时间都要来店里洗头发。但老秦说已经有段时间没见这个姑娘了。
她拿真发抵价为自己戴上假发
在这个假发店里,除了老秦外,还有一个20来岁的女店员,她是老板的妹妹小秦,在店里工作两年多了。她专职为客人剃头,尤其是女客人。“很多女孩进来的时候没什么,但一边剃头就会一边哭。”在店里上班时,小秦总是把自己的一头长发高高束起,既是方便工作,也为了不刺激到客人。
回忆起刚到店里工作时,小秦说当时每天都很压抑。“我以前从没跟癌症病人打过交道,更没见过这么多各种年龄层、各种病情的病人。他们有的绝望,有的平静,也有的要死要活……每天都有客人跟你倾诉,而你必须把这些信息照单全收。”
记得去年11月的一天,店里来了位个子很高的女客人,40多岁,穿着讲究,气质也好,就像时装秀里的“超模”。在店里看了一圈后,她停在一顶长卷发前。“这款多少钱?”她没有要求试戴,而是先问了价钱。“这款3300元。”听了价格,她脸上露出一丝难色,转而问老板:“你这里最便宜的是哪一款?”
从外地来上海治病,治疗费加上吃住,花销已近20万元。“我想选便宜一点的假发,能戴就行。”在老秦的介绍下,她挑了一顶360元的假发,但仍希望老板再打个折。老秦说:“这款300多元的假发几乎是成本价了,再打折成本都收不回来。”她停顿了下,摸了摸自己的头发,咬牙说:“我把我的真发卖给你,能不能抵200元?”当时她已经进入化疗阶段,头发慢慢掉落,一头长发略显稀疏。老秦最后答应把假发送给她当做抵价。
剃头发的时候,女人哭了。她说,自从生病以来,怎么看自己都不顺眼,以前买的衣服都没法穿,觉得自己很怪,不敢见人。“我以前烫个头发都要花一两千元,因为生病花销大,越来越拮据。这个病啊,真的可以让一个人的自尊心降到最低点。”发丝簌簌掉落一地。戴上假发,她专注地看着镜中的自己,半天才说了一句:“这是我吗?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
事后,老秦说,其实收客人的真头发没多少价值,只是给他们一个心理安慰罢了。
连丈夫都没见过她光头的样子
“东安路从斜土路到零陵路这一段,是癌症病人的‘安全区’。病人在这段路上可以不戴假发,但离开这个区域就要戴上。在我们店里可以剃头,在别的理发店就不行。让店里的人看到自己光头的样子无所谓,却死活不愿给自己的亲人看到。”老秦说,得了癌症的人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
赵阿姨定做了店里最贵的一顶假发。这天,她来店里取假发,进门便选了一张背对门口的座位坐下,一直低头看手机,不停咳嗽。她不愿与任何人对视,只要有人走进店里,她都会下意识躲开。
店员递上假发,赵阿姨摘下自己头上戴着的一顶便宜假发,换上定做的新假发,在镜子前端详着自己。“不行不行,显得脸太长了,我现在就像个鬼一样……”她满脸愁容。“您别急,我帮您修剪一下。”老秦一边给她剪头发,一边好言相劝,“您现在什么都别想,该吃吃,该喝喝……”
赵阿姨去年6月去医院做体检时还一切正常,没想到11月,身体突然感觉不对劲,再查已是癌症晚期。“我以前从来不去医院,医保卡里的钱都没花过。现在看到这个‘癌’字,是真的怕!一旦得了这个病,早晚就是一个死。如果我现在七八十岁了还好,可我才五十多啊。”
一共八次化疗,赵阿姨刚开始做第一次就知道头发要掉,就先剃了光头,花4000多元买了店里最好的一顶假发。白天出门,她戴上贵的假发,晚上睡觉就戴一顶便宜的。
“阿姨,这假发您不能一天到晚都戴着啊,皮肤会过敏的。”老秦提醒说。“不行,睡觉时我老公看到多难看啊!”自患病以来,连赵阿姨的丈夫都没看到过她光头的样子,每次她都要躲到洗手间里戴好假发才出来。头发修剪好,赵阿姨看着镜中的自己,终于有了点自信。她说,自己以前就是这个发型,现在看起来还一模一样。
生与死的剧目,每天都在这家小小的假发店里上演,他们习以为常,心照不宣。“到今年4月,我这个店就经营满4年了。”老秦说。
相关新闻
十七年坚守殡仪馆,赋予生命最后的尊严——最美退役军人徐申权
徐申权1987年入伍,作为部队里为数不多的光学技师,曾多次立功受奖的他于2003年转业到殡仪馆,成为一名普通的火化工人。17 年来,经他亲手火化的遗体有1300多具,安抚丧属5万余人
纽约官员发公开信 要求亚马逊将其第二总部设在这里
纽约官员发公开信 3月2日消息,据国外媒体报道,约80名纽约工会领导人、当地政府官员和企业主当地时间周五在纽约时报发表一份公开信,要求亚马逊再给纽约皇后区长岛城一次机会,将其第二总部设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