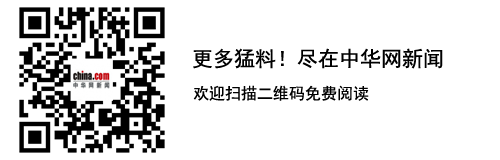云南推进极小种群野生植物保护 留住不为人知的美
云南推进极小种群野生植物保护
留住那些不为人知的美

图为科研人员对回归野外的滇桐采取保护措施。杨 静摄
核心阅读
这是一些极小种群野生植物:漾濞槭、华盖木、普陀鹅耳枥……
与一些“如雷贯耳”的濒危野生动植物相比,这些生存极度受威胁的极小种群野生植物的保护,尤其不容易。
但是相关的政府部门和科研人员从来没有放弃努力。
寻找、保护,希望最终能把繁殖的后代返还到自然界,并与生态系统协同发展,保护极小种群野生植物的成果正在显现。
赶在灭绝前被科研人员发现,漾濞槭从5株培育到上万株
走遍了整个山涧,都没发现新的植株——漾濞槭2002年被发现时,研究人员仅在云南省大理白族 自治州漾濞彝族自治县境内苍山西坡一个小山村附近找到残存的5株,其中3株还是当地农民砍伐后的木桩上冒出的新枝,只有两株开花结实。
尽管极度受威胁,可由于《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没更新,对漾濞槭来说,并不能享受法律层面的专门保护,只有基层保护机构和科研人员对其进行“挂牌”巡护。要拯救漾濞槭,仅靠简单的看护远远不够:野外播撒的5万多粒漾濞槭种子,仅保存下来7株成苗。发芽率低、幼苗被牲畜啃食,如果放任不管,漾濞槭想要在自然界恢复种群希望渺茫。
赶在灭绝前被科研人员发现,漾濞槭无疑是幸运的:通过更深入的野外调查,在附近山谷又发现了上百株漾濞槭;2015年,经过7年精心管理,栽培于昆明植物园的漾濞槭迁地保育植株迎来了第一次开花,这也是全世界第一株人工栽培的漾濞槭首次开花。2017—2018年,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所再次成功培育上万株漾濞槭幼苗,也将在原生居群附近进行定植。单纯从数量和技术上说,漾濞槭这一物种的保护取得了初步成功。
“一方面像漾濞槭这类植物亟待保护,另一方面对这类植物又缺少相对权威的描述,极小种群野生植物的概念实际上是被逼出来的。”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所杨静博士说,为了便于研究、公众宣传和获得国家层面的保护支持,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所积极参与,在云南率先提出了极小种群野生物种(包括动物和植物)的概念。
实际上,这一概念并非停留在学术上。为了抢救性保护面临高度灭绝风险的极小种群野生物种,2010年,云南省林业厅和云南省科技厅组织相关专家编制的云南省极小种群野生物种拯救保护规划纲要及紧急行动计划得到云南省人民政府批复。
2012年,国家林业局和国家发改委联合印发《全国极小种群野生植物拯救保护工程规划(2011—2015年)》,将极小种群野生植物拯救保护工作推向全国。
一旦某种野外种群消失,该种群的基因资源也随之消失
为什么会出现极小种群野生植物?据了解,地理隔离促进物种分化,云南山高谷深,物种数量繁多,但不少植物分布区域也相对狭窄,物种灭绝的风险尤其高。“也许是一场传染病,也许是一场山火,甚至可能是一次大规模滑坡,可能某个物种就没了。”杨静说。
“在野外,种子的生存环境本身就很残酷,别说跟其他动植物竞争,不少植物连自己的母株都竞争不过。”杨静表示,不少乔木尽管也会产生种子,但树木下落叶层较厚,产生的种子难以接触土壤,即便能够接触土壤,也可能由于树叶遮蔽阳光,难以成长;“这类种子要想长成树木,就要寄希望于动物将果实传播到较远的地方,但偶然性较强”。
仅分布于云南的孑遗物种滇桐,因当地种植草果、杉木、茶或者修路等,目前不足100株;生长在四川雅砻江流域的五小叶槭,目前仅剩500多株。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橡胶等经济作物的大规模种植,不少原生林成片消失。
“人类活动严重威胁极小种群野生植物的生存。”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所研究员孙卫邦介绍,有次为了找一株华盖木,团队整整花了4天时间,可终于找到的时候,却也很难开心起来:“华盖木应该是高大挺拔、很漂亮很潇洒的,但是我们找到的那棵华盖木树体却有斧头砍过的痕迹。”
为什么要保护极小种群野生植物呢?孙卫邦指出,极小种群野生植物中许多是具有药用、食用、保健、材用等经济利用价值的资源植物,而有些极小种群野生植物在生物演化历史上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对其开展研究有助于探讨生物演化的过程。如国家一级保护植物水杉,是我国特有的珍稀孑遗植物,对研究我国植物区系、古气候变化、古地理变迁及裸子植物系统发育有重要科学意义。
“对人类利用价值不大的植物,也许还没发现就消失了;但对人类有利用价值的植物,也未必就被人类进行科学地可持续利用。”杨静说。
实际上,以前遍布云南各山各谷的重楼属植物,不少已经很难在野外找到了。如今已经成为大宗药材的三七,更是被宣布野外灭绝。而随之消失的,还有三七的遗传资源。“比如野外可能存在部分耐旱、抗病种群,而随着野外种群消失,这一种群的基因资源也随之消失。”杨静说。
通过迁地保护、种质保存等,极小种群植物有了“备份”
如何更好地保护极小种群野生植物?“一是寻找,二是保护,接下来才谈得上系统研究与科学利用。”孙卫邦表示,极小种群野生植物保护最终要把繁殖的后代返还到自然界,让其在自然界形成自己的种群,并与其生态系统协同发展,实现它们在野外自然生境中的永久保护。为此,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已经初步建立了“种质采集—种质保存—人工繁殖—迁地保护种群的构建—野外种群及生境恢复”的技术体系。
自然更新快的物种,在适当的人为促繁下,保护效果立竿见影。弥勒苣苔保护小区实施已逾5年,保护区管理人员尝试过人工采种在保护小区内撒播,目前其成株由最初发现的640株增至2000余株。
在昆明植物园定居近30年的华盖木于2013年首次开花,但今年却可能没开花。“也许开了一两朵,我们没发现。”杨静说,不少木本类植物成年期很长,要想知道是否能够实现自然繁殖,周期也很长。
“萼翅藤在野外采集到的种子极为有限,目前只能通过扦插进行批量繁殖;而天星蕨至今仍未实现人工繁殖。”杨静介绍,并非所有极小种群野生植物保护技术都已经成熟,以滇桐为例,该植物从茎到叶进行组织培养都比较困难,目前主要通过种子繁殖。
也不是所有物种都像漾濞槭、弥勒苣苔这样容易实现人工繁殖。“一种是物种本身的问题。比如龙脑香科和壳斗科,种子是顽拗型种子,不能长时间保存,这样的物种要开展种质资源的保存就需要另辟蹊径;有的物种,比如说灰干苏铁,发现其野生种群以来,仅在2015年首次发现其雌雄株同时开花。大围山个旧管理所在咨询专家后,抓紧时间开展了首次人工授粉并获得了成熟种子650粒,但是种子萌发也是个难题。”孙卫邦说。
如今,通过迁地保护、种质保存等工作,不少极小种群植物至少有了“备份”。不过,杨静仍然认为回归自然不可替代。“建种子库保存种子,基于组培建立种质的离体保存体系都很必要,但不让植物回归其自然生境,植物的生态生物学功能就难以实现。”杨静说。
不过,要让“以前命悬一线的植物,以后长成一片”并非单纯的技术问题。专家指出,应考虑将有些极小种群野生植物纳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野生植物保护条例》明确保护的只有国家一级或者二级保护野生植物,目前的保护名录是于1999年颁布的,建议根据实际情况对名录进行及时更新。
链接
极小种群野生植物包括:野外种群数量极少、极度濒危、随时有灭绝危险的野生植物;物种或物种群体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要求独特、生态幅狭窄的野生植物;潜在基因价值不清楚,其灭绝将引起基因流失、生物多样性降低、社会经济价值损失巨大的种群数量相对较小的野生植物。
全国极小种群野生植物拯救保护工程一期拯救的120种极小种群野生植物中,有国家一级保护植物36种、国家二级保护植物26种、省级重点保护植物58种。(记者 杨文明)